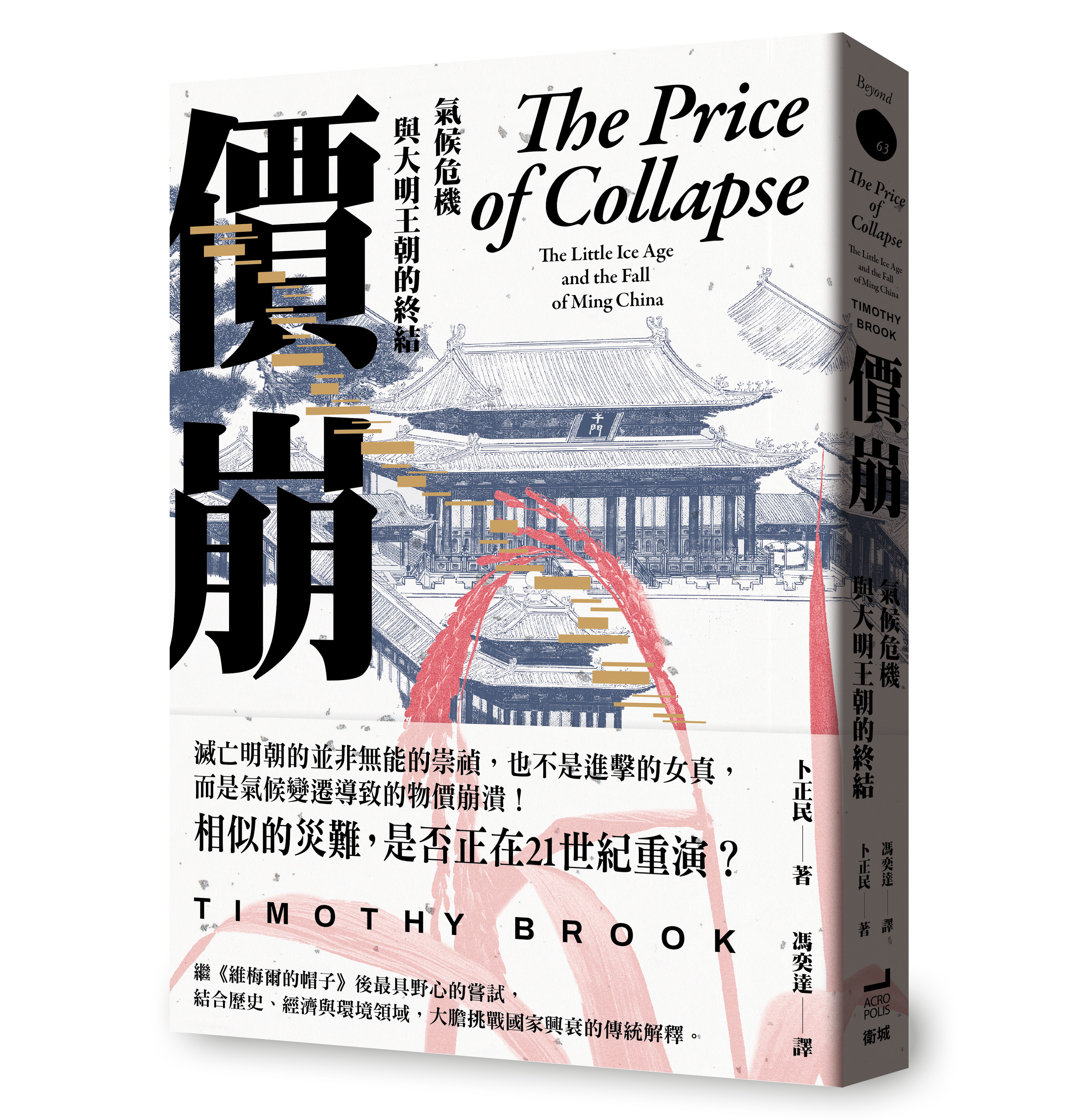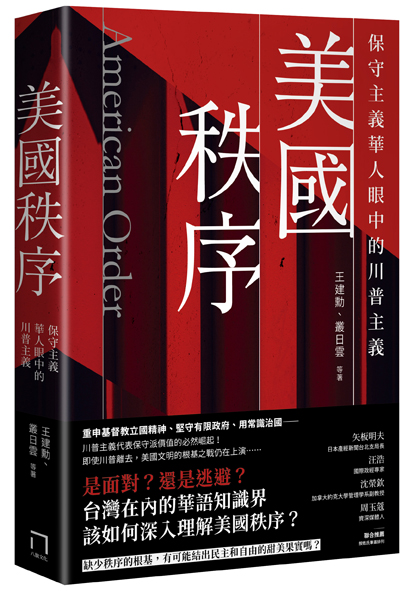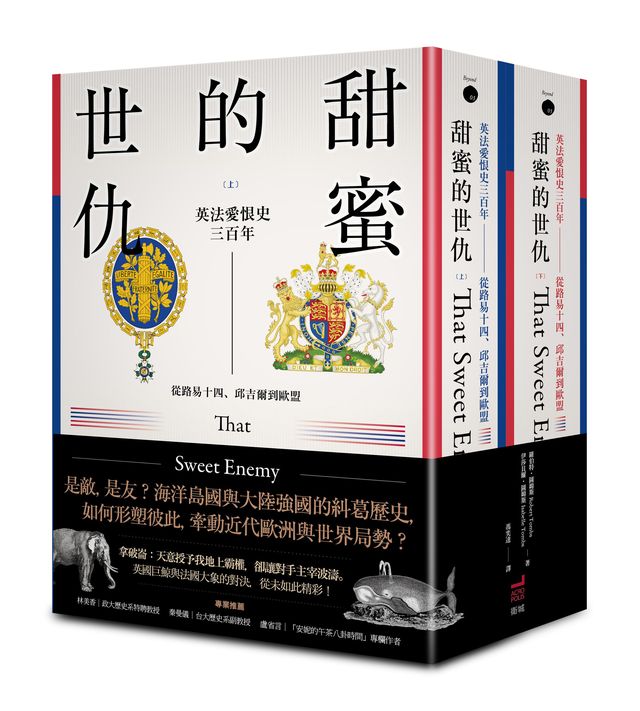緒論
今天,到達北京的旅行者看到的是一個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其物質性的歷史遺跡正在快速消逝,雖然過去的帝王居所紫禁城風采依舊,但其他一切都發生了變化。為修建環城公路和高速公路,高大的城牆已被夷為平地,拔地而起的高層建築將天壇的神秘氛圍破壞殆盡,以前國家祭壇的神聖禁地湧來的是普通的市民和遊客。遊客可能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已沒必要記住清這個自一六四四年到一九一一年統治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了。然而,這將是一個錯誤。
許多困擾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制定者的地緣政治問題都源自清朝。清(1644-1911)是統治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有人認為它是最成功的王朝。清也是最後一個征服者的政權。統治者來自東北亞,聲稱自己是建立金朝(1115-1260)的、統治過中國北部地區的女真人後裔。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一位名叫努爾哈赤的小部落首領成功地將許多東北部落聯合起來。其子皇太極(1592-1643)將這些不同的部落變成了一個統一的滿洲人群體。雖然皇太極在滿洲人進入明朝的首都之前就已去世,但學者仍然認為他是開創清帝國偉業的中心人物。
滿洲八旗軍在一六四四年席捲長城以南。在平定明朝境內的動亂之後,便轉向鞏固內亞邊疆,並在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劃定了與俄國的邊界,將蒙古草原、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納入了清帝國。清的征服奠定了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領土基礎,但隨著民族主義的發展,清的政策也產生了民族問題。他們認為自己是多元的多民族帝國的統治者。他們把居住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內亞邊緣地帶的民族看做帝國大業的重要參與者。這些帝國臣民與漢人地位相埒,他們操著各種與漢語相異的語言,篤信伊斯蘭教、藏傳佛教和薩滿教,在十八世紀,其各自獨立的文化和信仰系統,在清統治者的支援下得以發展和保持。這些非漢族群是如何被納入中國的民族主義體系的?這是一個至今仍未破解的謎題。
本書試圖從滿洲統治者的視角出發,探討清代歷史中的民族問題和歷史問題。它涉及近代史上的一個重大課題,即早期滿洲統治者的成功關鍵在於他們採取了系統的「漢化政策」。在一九一二年清滅亡之後,在關於如何界定這個民族國家的爭論中,出現了柯嬌燕所謂的中國歷史上的「漢化模式」之說。十九世紀末的中國知識份子如梁啟超者有感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向中國的讀者引介了「種族」和「民族」的概念。「漢族」一詞,意即「漢民族集團」,成為中國的政治語彙。由於其帶有血統、宗族的含義,「漢族」使中國人將這個國家「想像」為「漢族世系」。
漢族與種族合二為一。一些中國思想家認為漢族主導著「黃色人種」,這樣就可以展示一部傑出的文化成就史。滿洲人、日本人和蒙古人頂多只是處在「黃色人種」的邊緣地帶,有些作者甚至認為他們在生物學意義上不屬於黃色人種。後來被奉為「中華民國國父」的孫中山認為,中國之所以未能抵抗歐美的侵略,原因在於中國的統治者是外來的滿洲人。由於滿洲人不是中國人,不是漢民族的成員,所以清朝就缺乏全力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決心。孫中山試圖動員漢族起來推翻滿洲統治,創建一個漢族國家。
那麼誰屬於漢族呢?孫中山聲稱「漢族」是一個「純正的種族實體」。儘管史實表明許多不同的民族曾生活於中國,他仍堅持「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國人就是漢族或中華民族,他們具有共同的血統、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風俗──一個單一的、純正的種族」。歷史上侵入或遷入中國的不同民族與漢人融合:他們被漢化了。這就是孫中山在一九一二年之後發展起來的主要學說之一,當時他和其他民族主義領袖試圖在曾為清帝國之一部分的地區創建一個新的中華民族國家。雖然孫中山也偶爾談到有必要在中國眾多民族的基礎上構造一個新的「國家民族」,但他同時也認為少數民族最終會被融入佔多數的漢族之中。
正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所言,「近代社會的歷史意識基本上是由民族國家建構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和聚焦於民族認同的話語直接影響了中國的歷史學。依梁啟超的說法,擺在中國學者面前的任務是丟棄早期歷史的王朝框架而書寫「民族的歷史」。在民族主義者的日程表上,對那些曾統治過近代中國領土的非漢人外來征服者政權的描述,佔據了很重要的地位。在二十世紀二零年代,像傅斯年等人曾試圖將中國歷史說成是漢族的歷史。在中國疆土之內不同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歷史,則被重寫為中華文化(不管那文化可能是什麼文化)勝利的歷史。征服王朝也許純粹用武力擊敗了中國統治者,但他們都屈服於更為成熟的中國制度,並最終被融入中華文化之中。
《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柯嬌燕曾為之寫過評論)是芮瑪麗(Mary C. Wright)一九五七年的作品,該著作是適用於闡釋「漢化」的一個甚有影響的範例,它不僅回應了那些因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獲勝而指責滿洲人的作者(這些作者附和了孫中山的革命學說),同時也否定了那種認為遼和清這樣的外來征服者政權沒有漢化的說法。芮瑪麗指出,到十九世紀中葉,隔開征服者上層集團和被征服者的文化樊籬已逐漸消失,此時清統治者和中國的利益「實際上已難以區分了」。芮瑪麗在著作中以同治中興為例,認為同治中興源於中國儒家的政治思想,而改革的失敗也是儒家思想的失敗。
柯嬌燕列舉了數條理由,認為芮瑪麗關於滿洲人融入中國社會的觀點是錯誤的。即使如芮瑪麗所言,滿洲人的家園已被越來越多的中國移民滲入,清末旗人也失去了許多法律特權,然而這些變化卻未能毀滅旗軍駐防地的文化生活。柯嬌燕關於蘇完瓜爾佳氏的專著(編:《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用文獻充分說明這個旗人家族在清末民初仍保持著明顯的旗人特徵。在滿洲人和漢人眼中,滿洲人是不同於漢人的,這一點可以在太平天國叛亂和辛亥革命中得到證實。柯嬌燕認為,滿洲人肯定沒有消失在漢族之中,或者,由於漢人向他們展示出的敵意,他們也肯定不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更需指出的是,為了抵制不斷發展的漢民族主義認同,二十世紀的滿洲人也形成了一種現代民族認同。
在芮瑪麗寫作的時候,供學術研究所用的豐富的清代檔案資料還難以獲得。柯嬌燕對旗軍駐防地文化的研究,也是依據其他種類的資料。我的研究使用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內務府檔案,從而可以說明芮瑪麗的另一個看法也是不對的,而這是柯嬌燕沒有批評過的。芮瑪麗斷言同治時期的宮廷已漢化。而在柯嬌燕看來,「對宮廷生活的瞭解並不意味著就瞭解滿洲人在中國的生活……清朝諸帝的行為並不代表旗人」。目前所能獲得的檔案資料表明統治者還保持著滿洲認同。對這一狀況做出解釋,需要對該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學界對「漢化」這個概念的使用一直不多。例如,對滿語在宮廷使用狀況的研究幾乎都表明,滿語已不是統治者的首選用語,征服者的精英集團表明他們已融入了中國文化。但是,如柯嬌燕和我在其他論著中所闡述的那樣,忽視有清一代滿文文獻的歷史學家為自己的這種看法付出了代價。滿語不僅未在首都消失,而且還在新疆和東北的旗營中使用(參閱本書第一章),東北地區店鋪的雙語招牌和持久不衰的薩滿教傳統,使一位滿人學者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這個地區,滿洲傳統與其他少數民族以及漢人傳統共存,它們緊密交錯,以致難以分清彼此的面目。」
更為重要的是,滿洲認同不視某人將漢語或滿語作為其「母語」而定。十九世紀的清統治者使用起漢語來似乎更加得心應手,但那並不意味著他們不認同自己的滿洲人身份。認為滿洲人的民族意識來自於講滿語,持此觀點的人可以將之和講英語的情況進行比較。美洲殖民者雖然操著英語,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為自己建構獨立的認同,並宣佈脫離英國獨立。英語也未能阻止印度的民族主義精英利用這一語言促進印度的自治。因此,那些認為語言總是伴隨認同意識的看法是可笑的。
越來越多的相關輔助文獻表明,關於基本認同的建構和維持,這個議題不僅複雜,且具有歷史偶然性。民族性這一觀念是隨著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出現而得到充分發展的,首先在歐洲隨後在其他地區。正如柯嬌燕指出的那樣,將這一術語用於更早的時期是時代性的錯誤,是對歷史的扭曲。這並不是說清統治者缺少自我認同和認同他人的概念,不過,政治環境的要求和對自我的界定完全是兩回事。清的統治範式不是民族國家,統治的目標不是建構一種民族認同,而是允許多元文化在一個鬆散的人格化帝國之內共存。現代意義的民族性並不存在,同時國家也不想去創造這種民族性。
現代民族性不僅意味著創造出一個休戚相關的群體,而且要把它與其他群體區別開來。在女真人的故鄉東北亞,這些界限是很不固定的,三種不同的生態系統──蒙古高原、茂密的森林地區和肥沃的遼河平原──在該地區交錯在一起,使得依靠遊牧、漁獵和農耕為生的民族能夠互相交往。十七世紀的女真人以農耕為生,他們與蒙古人共用的詞彙顯示了兩個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女真人不僅講蒙古語,還用蒙古文字書寫,努爾哈赤的一些族人還採用了蒙古人的姓名和頭銜。依據有關八旗結構的蒙古文資料,大衛‧法誇爾(David Farquhar)揭示出,早期滿洲國家中的許多中國元素實際上是通過蒙古人傳入的。
滿洲人把來自不同文化傳統的人納入八旗組織,力圖把他們塑造為滿洲人──用同樣的法律、著裝規範和社會規則管轄他們。以前的各種認同意識被融入新的八旗認同中,至少在十八世紀之前是如此──到十八世紀,宮廷還很看重以血統來確定身份。即便如此,征服者精英仍然具有明顯的多元文化特徵。十八世紀新被納入清帝國統治集團的穆斯林、西藏人和蒙古貴族,使得征服者精英集團不至於具有單一的種族背景和認同。同樣地,儘管存在王夫之等主張「嚴夷夏之防」的人,但大多數儒家士子強調儒家學說的普遍性和通用性,認為他們的主要使命在於「教化」和「文化」,而不必在意種族或民族背景。在這兩大族群中,認同不是固定的,而是變化的。
此外,清的統治者對於文化問題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所關注的主題。作為個人,他們熱衷於保持愛新覺羅氏(Aisin Gioro)的血統和征服者精英集團的地位。然而作為統治者,他們不贊成那些可能改變其臣民固有文化的政策。他們是多民族國家的統治者,這決定了他們必須支持和促進臣民發展本民族的文化,並在帝國境內懷柔和籠絡不同的族群。在清滅亡之前,大多數清的統治者都會講多種語言:蒙古語、滿語和漢語。某些統治者(如乾隆皇帝)還不憚煩勞,學習藏語和維吾爾語。弘曆如是說:
乾隆八年始習蒙古語;二十五年平回部,遂習回語;四十一年平兩金川,略習番語;四十五年因班禪來謁,兼習唐古拉語。是以每歲年班,蒙古、回部、番部到京接見,即以其語慰問,不藉舌人傳譯……燕笑聯情,用示柔遠之意。
在十七世紀征服時期,順治和康熙皇帝試圖以儒家君王面目來贏得漢文人士子的支持。他們學習漢語,把儒家經典當做科舉考試的基礎,把科舉制度當做選拔官員的主要方式。滿洲皇帝支持和資助中國的藝術和文學,發佈儒教政令,改革滿洲人的婚喪以適應中國的習俗。孝道成為統治的主要先決條件。這些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儘管滿漢之間一直存在著根深蒂固的緊張關係,但是滿人的恩惠逐漸消彌了漢人的抵抗,贏得了他們對清王朝的支持。
清朝統治的各種漢化面向,以及對長城以南的前明領土的高度文治,使得許多研究者忽略了清統治者的非漢人出身,把漢化當做清代的歷史主流加以強調。本書各章的內容表明,清的統治者在觀念上從來沒有淡化自己與前明降民的區別,更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滿洲認同。當政治上有利的時候,他們就採用中國的習俗;當無助於他們實現政治目標時,他們就拒絕。清的統治者以同樣的熱情研究金代的歷史,吸收了金朝的許多政策。柯嬌燕分析了這些先例對清的統治的重要性:「在金代,利用科舉制度從百姓中選拔人才,並限制貴族擔任高級官位,是與金朝政府雄心勃勃的計畫相輔相成的。這些計畫是:限制貴族的特權和影響,加強中央集權,讓王朝的支持者在維護官僚制度中發揮廣泛的作用。這些做法都是大清帝國官僚政治的先例。
近年來關於十到十四世紀統治中國北方和西北地方的征服者政權的研究,對非漢人政權帶給統治者的顯而易見的政治風格提供了新解釋。契丹、唐古特、女真和蒙古統治者都曾把中國的官僚體制納入自己的統治中,但與此同時,他們改革中國的政治模式,以適應自己的環境。他們特別重視如何控制散佈在內亞和東亞的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所有的征服者政權都依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制定不同的管理政策,對不同的民族採取不同的法律,從不同的民族中選拔官吏。此外,雖然漢人被選拔到政府中做官,但這四個政權都拒絕漢化。每個政權都創造了自己民族的文字,都奉行兩種或多種語言的政策。每個政權都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不僅在儒家學說中,而且也在佛學領域為自己尋找統治的合法性。
清既不是對中國王朝的複製,也不是對以前的非漢政權的仿效。對大清的描述必須注意到統治者的非漢人淵源,而且還要進一步分析其統治技術的創新。本書不認為漢化是清的統治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相反,本書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清成功的關鍵因素是,它有能力對帝國內亞邊疆的主要非漢民族採取富有彈性的特殊文化政策。一般來說,中國本土的統治家族如果要奉行多元文化政策,則必須拋棄儒家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而清只需將以前異族統治者的模式加以擴大即可。這些發現間接地提示我們,需要重新考察早期內亞政權對中國歷史做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