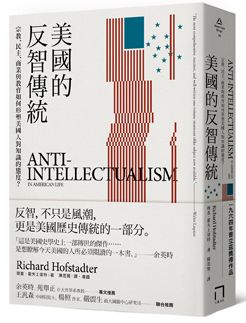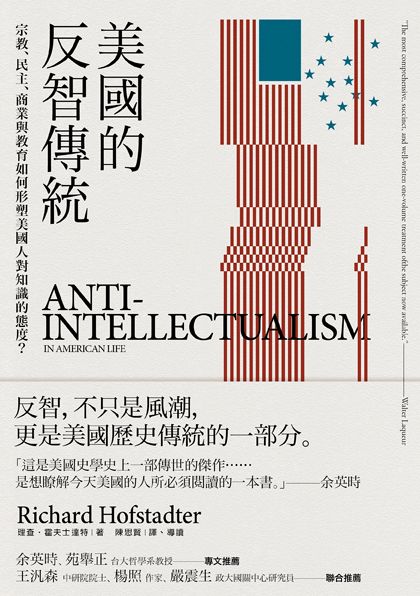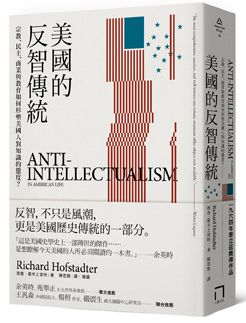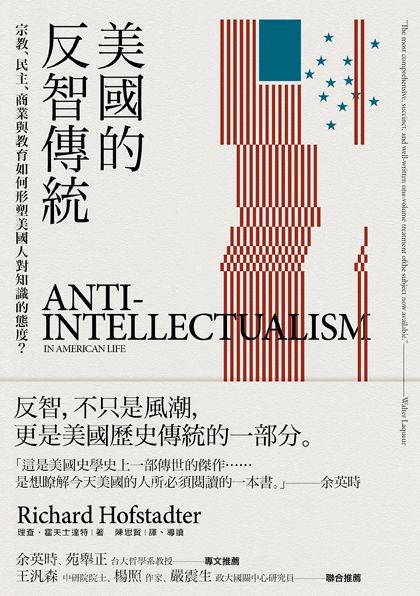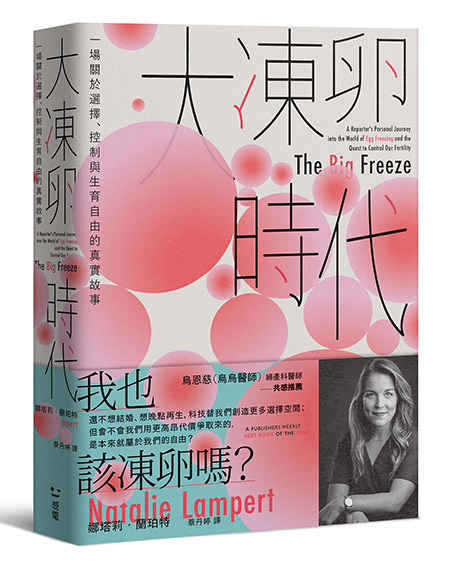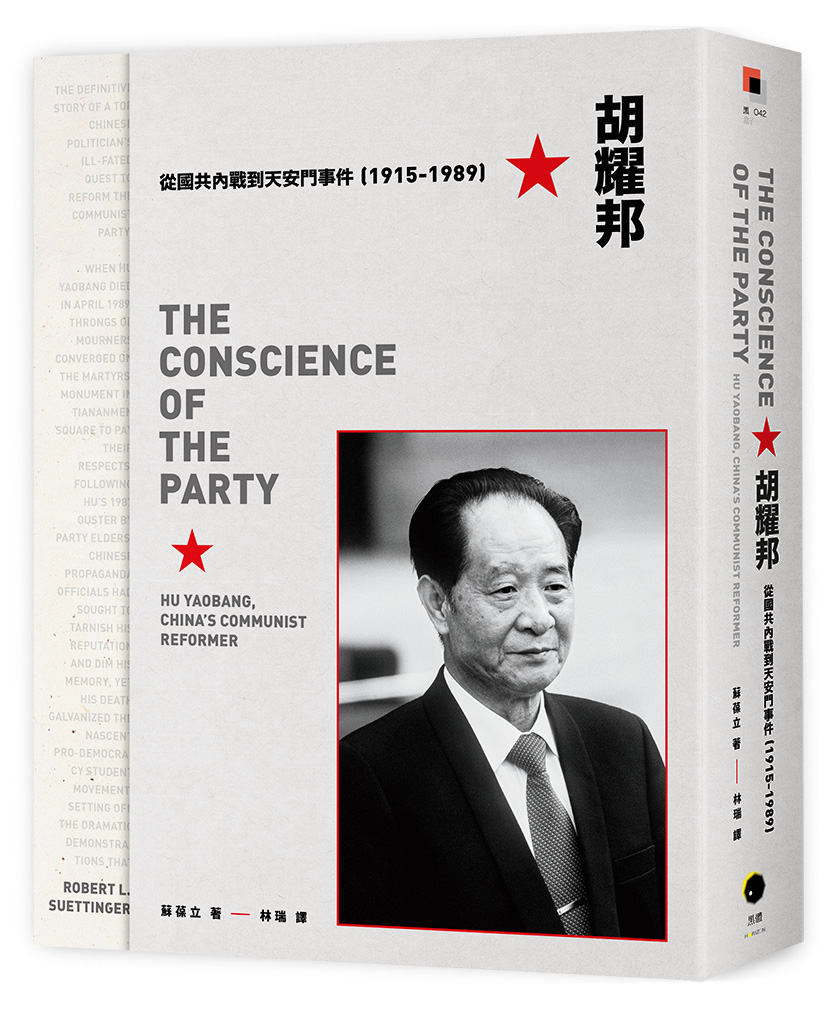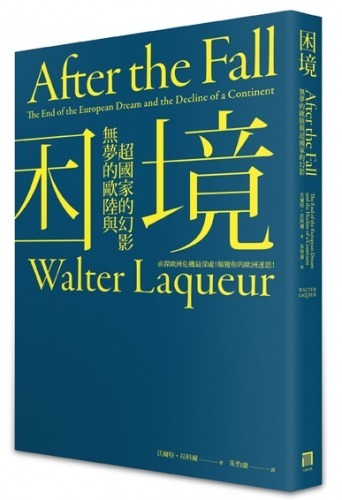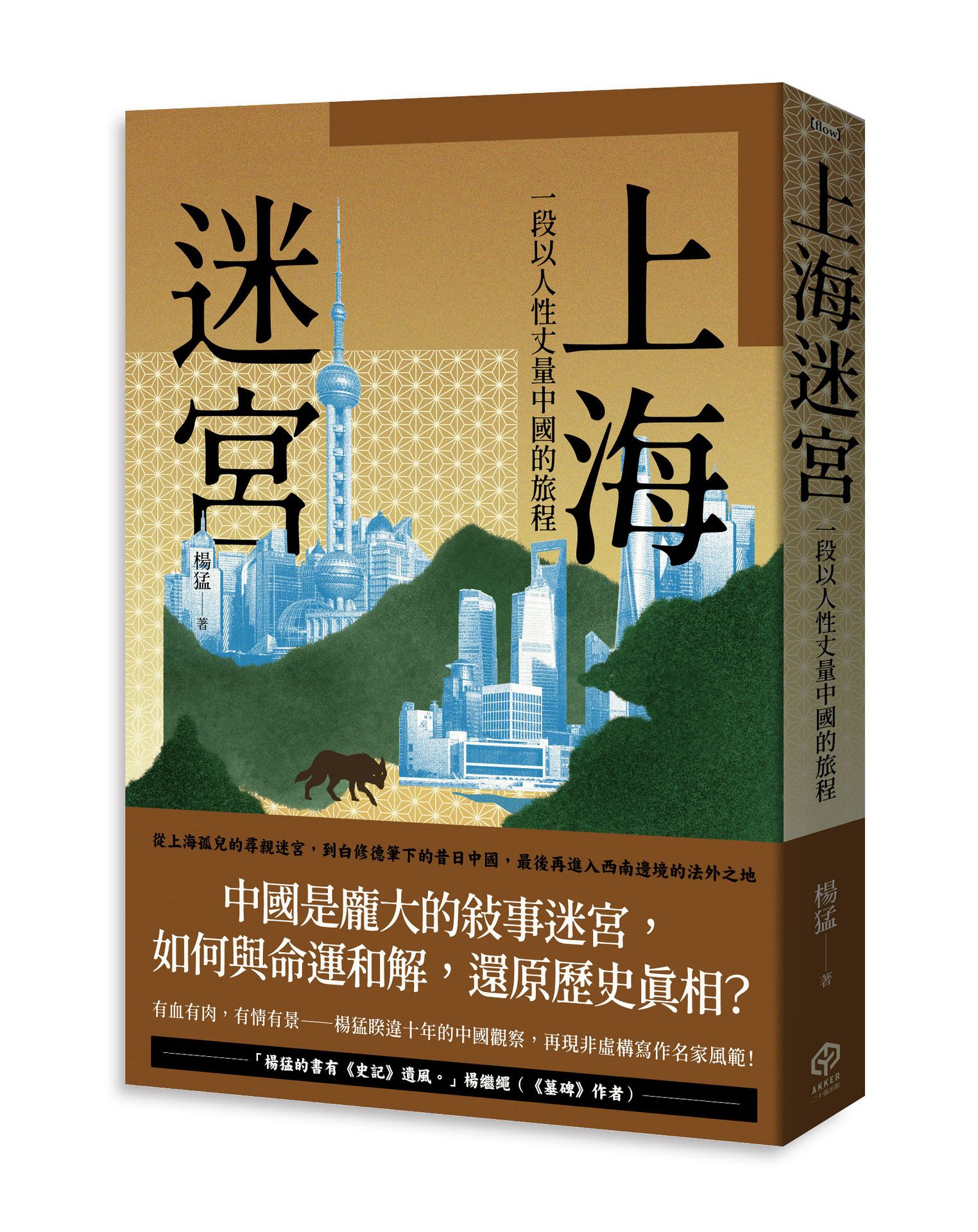反智,不只是風潮,而是美國深層文化的一部分。
兩屆普立茲獎得主--理查.霍夫士達特
從美國建國歷程、宗教傳統、政治體制、與商業精神中,挖掘美國的「反智」根源。
「這是美國史學史上一部傳世的傑作……是想瞭解今天美國的人所必須閱讀的一本書。」--余英時
「本書內容不但深深吸引我,也解答了我在美國生活時心中所累積的若干疑問,真的有恍然大悟的感覺。」----本書譯者、台大政治系教授陳思賢
美國,擁有傲視全球的頂尖大學與數量最多的諾貝爾獎桂冠,又以發達的科技與商業為世人提供了便利、舒適的文明生活。然而,美國文化卻少以精緻、優雅聞名,訴諸實用與庶民品味的大眾化商品與娛樂才見其所長。近年來小布希的窮兵黷武、川普的粗暴言論與政策更讓世人驚見美國文化中「反智」的一面,美國社會層出不窮的民粹與暴力事件也令人憂心忡忡。
活躍於二十世紀中葉的理查.霍夫士達特是少數最早注意到美國文化中的「反智」現象的學者之一。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教授,他深深感受到美國人對純粹的學術--包含深厚的人文學養、抽象的理性思辨等--的漠視與敵視,尤其是五〇年代以反共為名卻動輒以知識分子為標靶的麥卡錫主義,更另人痛心疾首。他於是於一九六三年出版了這本結合了思想史、社會史與政治史的《美國的反智傳統》,對「反智」做了有系統與歷史深度的爬梳。
《美國的反智傳統》指出,「反智」不只是一時的民粹現象,也未必只是理盲躁動,它反映了美國人在特殊歷史與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傳統。脫離英國而獨立建國的經驗讓美國人往往視歷史為落後、腐敗、封建貴族對平民的剝削的象徵。在美國蔚為主流的基督教福音教派推崇教友發自內心的感動,以及與上帝的直接溝通,而揚棄神學考據。富蘭克林、亞當斯等建國先賢雖然具備偉大的心智,但對平等的堅持使得美國政治很快轉向以純樸、勤奮、踏實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訓練的庶民百姓為主體,知識分子與仕紳階級淪為邊緣。蓬勃的商業文化更將美國的教育制度導向實用目的,而輕視博雅的人文薰陶。於是我們會看到,起草《獨立宣言》的傑弗遜竟因為學問太好,被批評不夠格做總統;老羅斯福靠狩獵技巧贏得選民青睞;鋼鐵大王卡內基批評大學教育對做生意有致命的傷害;田納西有眾議員以不會寫自己的名字而自豪,密西根州給老師的薪水比清潔工還低,以及全美百病叢生的公立教育系統……
美國本就是由對歐洲的壓迫與頹廢不滿的人所建立,
他們醉心於美洲的不是在此萌芽的社會,而是自然與野蠻。
霍氏傑出之處更在於他固然一面嚴加批判民粹、保守、極右的反智思維,卻也試圖挖掘其背後深層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予以同情性的理解。因此本書不但是研究美國文化與思想史的巨著,更可以透過它去思考一個更宏觀的主題:「智識」在人類文明中如何可能?知識分子能在社會上扮演什麼角色,又該如何與權力共處?
《美國的反智傳統》於六〇年代甫上市就造成轟動,並接連獲得普立茲非小說類獎、愛默生獎與希爾曼獎等殊榮。在美國之外本書也掀起廣大迴響。當代華人史學泰斗余英時先生於1975年撰寫的〈反智論與中國傳統〉即是受到本書的啟發。半個多世紀後本書中文版終於上市,讀者將可見其歷久彌新、經得起時代考驗的深厚史學造詣。
理查.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
二十世紀的美國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教授。霍夫士達特曾兩次得到普立茲獎:他憑藉在《改革的年代》(The Age of Reform)中對1890年代民粹運動和二十世紀初期進步運動的理性分析首度於1956年獲獎,之後又因《美國的反智傳統》中對文化史的研究而於1964年再次獲獎。
除了上述兩書之外,他尚著有《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1944,民國七十年由聯經出版)、《美國政治傳統》(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1948),以及《美國政治中的妄想偏執風格》(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1964)。他也與華勒斯(Michael Wallace)共同主編《美國社會的暴力:一部真實記錄》(American Violence: A Documentary History, 1970)。
陳思賢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政治學博士,專長為西洋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
著有《西洋政治思想史:古典世界篇》、《西洋政治思想史:中世紀篇》、《西洋政治思想史:現代英國篇》、《西洋政治思想史:近代英國篇》。譯作包括《政治的意識形態》。
幾句推薦的話--余英時
推薦序--苑舉正
譯序與導讀--陳思賢
作者自序
第一部份 序論
- 這個時代的反智現象
- 智識不受歡迎
第二部分 基督教信仰
- 福音運動的衝擊
- 福音主義與振奮派
- 對現代性的反抗
第三部分 民主政治
- 仕紳的沒落
- 改革者的命運
- 專家的興起
第四章 社會文化
- 商業與智識
- 白手起家與勵志型信仰的出現
- 其他領域所發生的智識無用論
第五部分 民主社會與教育
- 學校與老師
- 生涯發展導向的高中教育
- 兒童與他將面對的世界
第六部分 結論
- 知識分子:與社會疏離或被同化
謝詞
註釋
(一):第二章 智識不受歡迎
反智的定義
若有些人一直懷疑「智識」乃是顛覆社會的力量,則一昧向這些人解釋它其實是很安全、溫和與怡人的東西,是絕無效果的。其實若干守舊派及強硬的俗民派有時是對的:「智識」是危險的東西。如果讓它自由發揮,則它會翻案許多事情、深入地分析與質疑很多事情。杜威(John Dewey)曾說:「讓我們承認保守派說的吧!當人類開始思考時,沒有人能保證後果會是怎樣。我們只能知道因此許多事物或制度會瓦解。每一個思想家都在拆解掉這個穩定世界的一部份,沒有人知道毀壞後什麼東西會出來代替。」此外,沒有人可保證知識分子階級會審慎克制其自身影響力;但對於任何一個文化,我們可確知的是:禁止「智識」的自由使用會比開放其使用來得糟多了。其實與那些保守的文化糾察隊比起來,知識分子總的來說並不會顛覆社會的。但是「智識」的作用是永遠在反對某些事情或是加以暴露、嘲諷:例如,它經常成為壓迫、欺騙、虛妄、教條或利益勾結等事的敵對力量。
幾個世代下來,那些受「智識」之害或是畏懼、憎惡它的人,早已發展出一種關於它的迷思──它究竟是什麼,以及它在社會中的角色為何。當今反對「智識」的人已不需要創造新的說詞,因為這種迷思早就深植人心。本書稍後的章節將會仔細說明這個迷思在美國是如何發展與持續下來的。現在我們先簡單概括地說明「反智」心態背後的基本假設是什麼?以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它們。
「反智」是建立在一組虛構與抽象的敵意之上的。他們把「智識」與感情(feeling)對比,因為他們認為「智識」缺乏溫暖的情感。「智識」也被與品格(character)對比,因為他們認為「智識」代表聰明,而聰明很容易就變成狡猾或是邪惡。它也被與腳踏實地操作(practicality)對比,因為理論總是被與實踐並提,而「純粹」理論的思維常被瞧不起。它被與民主對比,因為「智識」常被認為特異超群而與平等相悖。當這些看法被普遍接受時,則「智識」或是「知識分子」就成為落水狗。誰想要犧牲掉溫暖的情感、堅固的品德、實踐的能力與民主情懷去逢迎一個至多只是聰明但最遭可能是邪惡的人呢?
當然,這些虛構的敵意的基本錯誤,在於未嘗試找出「智識」在人類生活中的真正極限何在,而是將它與人類其他特質強加對比。其實無論在個人或人類歷史中都不適合將問題以如此簡單抽象的方式呈現。同樣地,我們也不適合在這樣的質疑下去為「智識」辯護,例如它與感情、品德或是實踐力的對比是如何。我們不應將「智識」看成與人類其它特質形成零合競爭關係,而應將它視為可讓這些特質更好更完美的因素。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會否認「智能」是人類尊嚴的表徵之一,或者至少是人生中需要的能力之一。如果我們把心智(mind)看成是感情的指引力量而非威脅,「智識」既不是德性的保證也非危害,把理論看成有用的而非必然是比實踐差的東西,把民主提升到可以容許傑出優異的人或事,則前述的敵視就不會發生了。如照這樣來想,問題就迎刃而解;但歷史上卻少有人這樣認為,所以本書的目的在追溯我們歷史中的若干社會運動,在其中「智能」從可協助成就其它道德到被抹黑為一種特殊的罪惡。
首先,我們要從美國的宗教史去追溯「反智」。這不單是因為理性主義與信仰的對立由來已久──儘管這本是人類永恆的困擾──而是因為無論現代宗教思想或俗世思想本身都在宗教史的演化中被決定。不管在任何文化中,只要宗教是屬於心靈(heart)與直觀(the intuitive qualities of mind)的領域,則理性就無用武之地或是被看成較低下,因而變成是無意義甚至是危險的。而只要一個社會對其內部有學養的知識階層不信任,就會加以攻擊或是貶抑,這對宗教界與俗世的知識分子皆然。在當代,「福音教派」(evangelicalism)是沿襲這種宗教性「反智」心態的最佳代表,它也因此是堅決的「反教儀主義」(anti-nomianism)。美國並不是唯一的福音教派社會。但是美國的宗教文化大抵是由福音派主導的,也就是說,在福音派與傳統基督教間美國是一向傾向於前者的。理由何在?我們只要看英國的宗教史就可知:在英國傳統教派一直必須致力於吸納與馴化那些較自由激進的福音運動,也就是說福音運動處處挑戰傳統教會;而在美國,福音運動快速地顛覆與替代了傳統的聖禮儀教會(liturgical churches)。
此處我們必須交代福音教派中的原始主義(primitivism)這個問題,它在美國社會影響廣大,但本書中我們不對它單獨處理而是與福音主義一起討論。原始主義一方面與基督教有關,一方面與異教有關。它的迷人處也許在於一個基督徒因此可以享受一點異教徒能有的自由或儀式,或是反之──異教徒可以從原始主義中領略信仰的意義。在有些地方原始主義鼓勵人們追求早期原始基督教的精神,也激勵人們恢復大自然給人的原始能力,而人可因此接近大自然與上帝──雖然二者的差異何在並不清楚。在這種心態中,會有尊崇直觀的「智慧」(wisdom of intuition)勝於「理性」(rationality)之傾向,因為前者是自然而由神賜的,後者是人文教養出來的。
在西方與美國,原始主義由多種面貌表現,它一直是重要的傳統。即使身居知識分子階層的人對人類文明的繁文縟節式虛榮或種種人為規範約制不滿時,回歸原始主義的呼喚就會冒出來。在美國,原始主義影響了很多有教養文化的人,他們雖然不會去過著像西部拓荒者般的生活,但是對於文化的虛矯卻不以為然。在新英格蘭「超驗主義」(Transcendentalism)中我們明顯可見此思想──這簡直可謂是知識分子的福音主義。從帕克曼(Parkman)到班克羅夫(Bancroft)到透納(Turner)的著作,這樣的想法一直都在。美國很多作家對於印地安人與黑人的看法正是如此。從著名的西部開拓者如布恩(Daniel Boone)與克羅凱(Davy Crockett),到西部電影中都有這樣的想法,而這樣的流浪冒險者文化傳統深入人心,以致於小說家勞倫斯(D. H. Lawrence)曾說:「美國式的心靈基本上是鋼毅、孤獨、堅忍的,其實就是一個殺手。」而作為性方面的神秘魅力,原始主義思想一直是美國文學上的重要主題,屢屢出現在深受奧地利心理學家萊希(Wilhelm Reich)影響的美國作家的作品中。而美國政治上展現的原始主義,則傑克遜總統(Andrew Jackson)、弗里曼(John C. Fremont)、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與艾森豪總統等人的公眾形象皆是有名的例子。
這並不意外:美國本就是由對歐洲文明的壓迫與頹廢不滿的人所建立,他們醉心於美洲大地的不是在此萌芽的社會制度,而是自然與野蠻。尋找世外桃源,離開歐洲奔向原始大自然的心態,重複地反映在殖民者從東岸向西部拓荒的歷史上。一次又一次地,美國人的心靈想要離開組織緊密的文明社會,因為文明一再地將枷鎖套在人身上;人類也許無法離開文明整體,但是其中有些東西的確讓我們窒息。
(二):譯序與導讀
陳思賢(台大政治系教授)
對我來說,可能翻譯比著述還令人頭疼。但會選擇這本書,從頭到尾把它譯出來,實有其因緣。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震驚世界。八旗文化的編輯王先生(也是我20年前教過的學生)正好告訴我這本書,我們兩人都同意,若有人想將這本書介紹給中文讀者,此其時矣!這本書不但內容深深吸引我,也解答了我在美國生活時心中所累積的若干疑問,真的有恍然大悟的感覺。因此當下就決定暫時擱下一些事把這本書翻譯出來,與大家分享我對美國文化的這種「重新認識」。
美國的歷史實在太獨特,她是一個移民國家與墾拓社會,當初五月花號的清教徒來此是因為逃避宗教迫害,而後來的移民則多係憧憬追尋經濟機會,更後面又有不少戰爭與政治難民湧入。每個人來到此地的時間先後與理由動機不同,但是最後都會在所謂「美國文化」的籠罩下生活。相對於歐洲與亞洲的古老國家,「美國文化」很新,很年輕,大家也會對它的特色作不同的形容,但是用「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貫穿其中,這倒是聞所未聞。
然而作者並非市面上一般語不驚人則不休的商業性寫作者。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美國史講座教授,著作等身,獲獎無數;會用此主題來「思考」美國文化──對外人算是「介紹」,對自己人應是「反省」──動機必然是很嚴肅的一件事情,更是發人深思。他在半世紀前出版此書,並獲得普立茲獎(The Pulitzer Prize),可惜當時的歷史氛圍下(二戰後美國黃金歲月時期)社會對此主題不會有太多的重視,大概只有專業歷史研究者與書中的主角,也就是知識份子,對他的「美國史新詮」,會有興趣。但是今天可不同了,美國國內外情勢在這數十年間逐漸地變化,以至於產生了現在這麼一位「特別」的第45任總統,那麼如果要問何以如此?本書就是最重要的解答泉源之一。
川普就任掌權以來,至今風波不斷。他從開始競選後的諸多言論到就任後的政策皆引發廣泛爭議,例如反移民、反社會福利、反重稅、反伊斯蘭、反環境保護與反對介入太多國際事務等,但其實在這些問題上都有一條隱性的軸線牽連著,或是由微妙複雜的因果關係來引導著,那就是──他的主張都是針對某一個特定群體的喜好與利益而發出。因而這個群體形成支持他的最大一股民粹洪流,他當初應也是在體會到這股力量後才決定參選總統與定調競選策略的。顯然地大家都知道,川普的這些言行都與種族主義與白人優越主義心態有關,也就是歐洲許多國家「極右政黨」理念的「美國版本」。
但我們試看,其實反移民與反重稅、反環境保護等本是兩種本質不同的問題,分屬兩個戰線。一個是排外、種族主義的問題,另一個則是典型的布爾喬亞資本主義心態。很多中下階層的美國白人受經濟不佳影響而失業,或是必須屈居忍受低收入、高所得差距,因而開始仇視外國(尤其是亞洲經濟體,1980年代底特律的華裔陳果仁命案即是一例)與移民。但殊不知這些(引進廉價移工或是看上國外廉價勞力因而企業大量外移進行海外投資)都是資本主義政黨與政策的結果,這種政策大大嘉惠跨國企業與大資本家,以及持有這些企業股票的中上階級,最後的高失業率與社會所得差距惡化概由小老百姓與藍領階級承受其痛苦。而到最後情況很嚴重時,種族主義者登高一呼,所有受害者反而聚攏來支持當初造成他們困境的右派資本主義政黨。這無疑是因果不分,認識不清,人類最原始的「非我族類」情懷被挑起後的直覺與感性式的反應。這就是民粹政治。
但美國不是第一次有民粹政治。半世紀多前的一九五〇年代,翻攪社會的麥卡錫事件(McCarthyism)也是血淋淋的例子。這些「民粹」式感情背後都有某些共同的成分:視野狹隘、對現狀認識不清、任由某種情結與情懷無限發酵,以及對於智識、發展與進步的害怕、複雜情緒。本書作者的最原創性與最大貢獻,就是把這些不同的因素溯源或是歸結於一種特殊的心態,他稱之為「反智」。這成為了本書的主題,他也企圖在美國歷史的各個面向中追溯這種心態的成因。但這無疑是個龐大的工程,因為這要涉及對於這個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社會,幾近於全面地檢視其演變過程。霍夫士達特真不愧是一位榮獲普立茲獎的傑出歷史學家,他所擬出的解釋架構讓我們知道,這個研究將不會是一個小品或是小題大作式只求言之成理的專題報告,而是必須有極大勇氣面對堆積如山史料的嘔心瀝血嘗試。他準備從美國這兩百年來宗教、政治、社會與教育四大面向,來檢討這個民族歷史上「反智」心態形成的原因。
我們可以先來看看下面這一段對於美國「反智」傳統形成的最精簡扼要敘述:
如果福音派與原始主義開啟了美國人的「反智」意識,則後來的商業社會確保了「反智」是美式思維的特色。從托克維爾(Tocqueville)開始,研究美國的人大都認為在這個國家中,實際的商業主義壓過了思考與玄想。民主政治與商業至上的美式生活,培養出一種心態與習慣,就是凡事需要迅速作決定、快速反應以抓住機會。因此深入、細膩與精確的思考並不是美式生活所鼓勵的。平民大眾從日常生活中累積出的經驗與直覺才是最可貴的人生指引,也是支持美式民主背後的共同價值觀,而過於深奧的美學、哲學或宗教理論其實不但不實際,還會讓世界更混亂。
大家都知道美國的歷史主要是由清教徒移民新英格蘭開始的,也就是說,這塊土地與宗教間的關連要早於與其它任何因素──例如經濟──的關連。但是來到這裡的人要生存、要墾荒、要建立新家園、新天地,於是稍後「經濟」、「政治」因素便出現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變化,隨後又回過頭影響了宗教,使得美國的十八、十九世紀的宗教景況大大不同於十七世紀的清教徒時期。十八、十九世紀美國宗教最重要的現象就是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與振奮派(revivals)的出現,這些都強調信仰的感性面向,也就是作者所稱的religion of the heart。這樣的信仰方式很適合於在艱苦中掙扎、奮鬥求生存的拓荒者,他們沒受什麼教育,沒有深究神學名詞或教義爭議的興趣,只企求福祉與恩典,只尋求心靈上的支撐與慰藉。於是他們歡迎簡單直接訴諸情感的宗教方式:平易親和的牧師與簡易振奮的講道,「與智識愈近,離上帝愈遠」。作者認為,這種下了美國「反智」傳統的第一個種籽。
接下來的第二個原因,卻有點兒令人納悶。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有成文憲法的民主共和國。美國式民主的特色就是生而自由、人人平等。這種憲法特色(制度上)與社會觀念特色(文化習慣上),使得美國式的民主一直有著實用主義與平民化的風格。如所週知,這個國家在創建初期,因為有傑出的建國始祖的擘劃與他們種種令人景仰的事蹟才因此偉大,但是弔詭的是:他們卻制訂出了一個讓菁英逐漸退場或自廢武功的憲法、憲政慣例與政治制度。所以自從十八世紀建國後,十九世紀美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商業民主社會,在此中做為市場上最大消費者的一般百姓、平民大眾成為社會價值或輿論的主流,當然在貨品上與精神品味上處處迎合他們的商人,也就順勢成為權力掮客,菁英與知識份子慢慢退場。政治由商人與商業主導,這就是美式民主的真髓。而實用主義的社會文化強調經驗與直覺,成功靠的是奮鬥意識與果斷堅毅,抽象的理念與智識很容易被譏為「象牙塔內的遊戲」。不意外地,「反智」成為市場價值與商業文化下的必然結果。
最後,作者花了大篇幅討論美國的教育史與教育思想史。在本書探究的主題中,為何教育重要?因為教育「鞏固」與「傳遞」了「反智」心態。作者認為,任何人在討論美國教育時,最重要的一個先決認知就是:美國的教育受美國的民主制度影響很大;可以如是說,許多人認為美國教育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教育出能夠支撐這個大眾化民主、商業民主社會的國民。因此,延續公民社會特質所需要的「政治社會化」與發展經濟所需要的「職涯技能」,才是美國教育的最重要目標,而不是「智識能力」與「學科專業能力」。在這種觀念下,普及的國民教育與遍佈社區的公立高中就成為美國教育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特色。這種教育要訓練的不是準備進大學的學生,而是美國式民主所需要的公民與適合美式社會生活的新成員。當世人都在訝異美國高中生學科水準低下(尤其是數學與科學)的同時,美國教育的設計者卻在欣喜他們所教出來的學生有足夠的生活經驗與判斷力可以走入社會。因此可能令所有外國讀者驚訝的是,作者認為至少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反智」乃是美國教育政策設計者至少在潛意識層次所抱持的目標。
所謂的「反智」,對於崇尚智識、尊重士大夫的東亞文化來說簡直是難以理解。我們現在雖然已經不會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態,但是也很難會去鄙視、貶抑「智識」。東亞文化傳統中,由於對智識的尊重與儒家式家父長文化殘留較深,所以知識份子扮演的角色吃重。因此我們的社會面臨的是跟美國不同的問題:美國的「反智」傳統造成了民粹浪潮起起落落,對於智識菁英愛恨交織,所以有時並不是第一流的人在領導國家;但是我們的困擾卻是,受社會所倚重的智識菁英在獲取權位後是否會背棄良知?在追逐權力與實踐理想的拉扯中,智識菁英是否有維持格調的信念與勇氣?儒家傳統中有所謂「道統」與「政統」間的制衡,就是指知識份子應該有的自我把持與人格尊嚴之所在。當東亞文化傳統中的知識份子受到權力誘惑而背棄自身理念時,那還反不如西方政治中的商人實用主義赤裸裸追逐利益來的坦然,畢竟後者乃是資本主義下的自由主義民主的運作邏輯。令人訝異地,霍夫士達特在最後結論章節中,竟然花了大篇幅去討論知識份子的角色責任與試煉。依本書的邏輯,這本來不應是美國這樣的社會所面臨的重要問題。所以現在弔詭的是,本書前五部份,我們是懷著趣味在看美國歷史上「反智」現象之形成與演變,有些地方令人莞爾,有些幾乎捧腹,但我們是旁觀者;可是到了最後一章關於知識份子角色的嚴肅討論,我們必須坐直端看,好好想一想了。
本書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一個時代中最傑出的作品。它的優秀,不但符合一般常見的標準,也就是資料充實、敘事富於洞見與技巧,及析論深刻等,它更有一個獨特的優點,那就是作者的「勇氣」。如果作者全書想要論說證明的主題確實為真,那他不啻在整個美國社會之前「起訴」、「控訴」現在與過去的美國社會──他正指著許多同胞的鼻子大肆批評!從原著的迆邐行文、韻采婉約的書寫風格,或是從容優雅、信手拈來的博雅學養來看,作者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典型文人/知識份子。他自己就是書中他頻頻隱於敘事之後為之打抱不平的受害者。所以如果這真的是一個有著「反智」傳統的社會,他的結局會是什麼?──這就是他的結局:他的「同類」頒給了他普立茲獎,但是這本書就此石沈大海,缺人聞問了。
本書作者霍夫士達特早已於1970年離世,快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把他的書重新「出土」,彷彿是偶然,依稀也是必然。美國2016年的大選,讓我們想起有這本書;當我們仔細讀完這本書後,就會發現,它其實早已預言了今天(所以遲早,美國人會被迫再度面對這本書)。從述說一個社會從哪裡來,它預示了會往何處去。這何嘗是容易的事?更何況他可能本來也沒有這樣的野心。但是,從對美國人在宗教、政治、商業與教育的「成長歷史」與「心態」(mentality)作了如此深層的剖析後,他如同已經替這個社會批了「八字」與「紫微斗數」。
但是否真的這個社會「命格已定」?霍夫士達特在他有生之年看見了一九五〇年代民粹風格的艾森豪/史帝文遜(Eisenhower vs. Stevenson)大選與麥卡錫事件,而他身後的今天我們目睹由激情主導的「反恐戰爭」與2016大選。在這些事件中,美國社會都拋棄了知識份子而任由其它的因素猖狂蔓延引領大眾。我們須知,知識份子並非必然適合擔任領袖,但是「智識」與公共知識份子的襄助輔佐卻是任何一個社會所不能缺少的,否則這個社會不是流於紛亂(眾多俗世利益間的無止盡競奪),就是缺乏靈魂與精神力量的平庸。當然,我們此處指的「智識」是在道德與淑世感之下的經世「智識」,而非指專業技術上的知識。後者與整體社會精神的提升無關,只是一種生產力。真正的「智識」,具體的表現在於促進「公益精神」(commonweal)之上,而通常來說它可被社會上各種不同群體與職業的有心之士所實現出來,但最集中地可能乃是由若干公共知識份子所展示出來。公共知識份子是「智識」與「公益精神」間最直接的橋樑,他們是任何一個共和國中的政治安全瓣。美國的公共知識份子如果消失匿蹤,那麼這個國家終究會永久淪為「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格局。
霍夫士達特在書尾對於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大力著墨,無疑是帶出了一個全書主旨之外的嶄新命題。當我們對於經世的「智識」用促進「公益精神」加以定義後,就不妨回過頭來看看為什麼、或是在什麼情況下,一個社會的公共知識份子群體竟會無法出現?一個最驚悚的答案會是:知識份子自己開始「反智」,他們把促進「公益精神」的「智識」藏在個人偏私的情感或是利益之下了。於是,一個共和國就可能成為一個各方競逐利益的「市場」,人類文明當然可以在「市場」中延續下去,但是很難提升。故總結看來,這本書,確實是含有「春秋之筆」的重大旨意在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