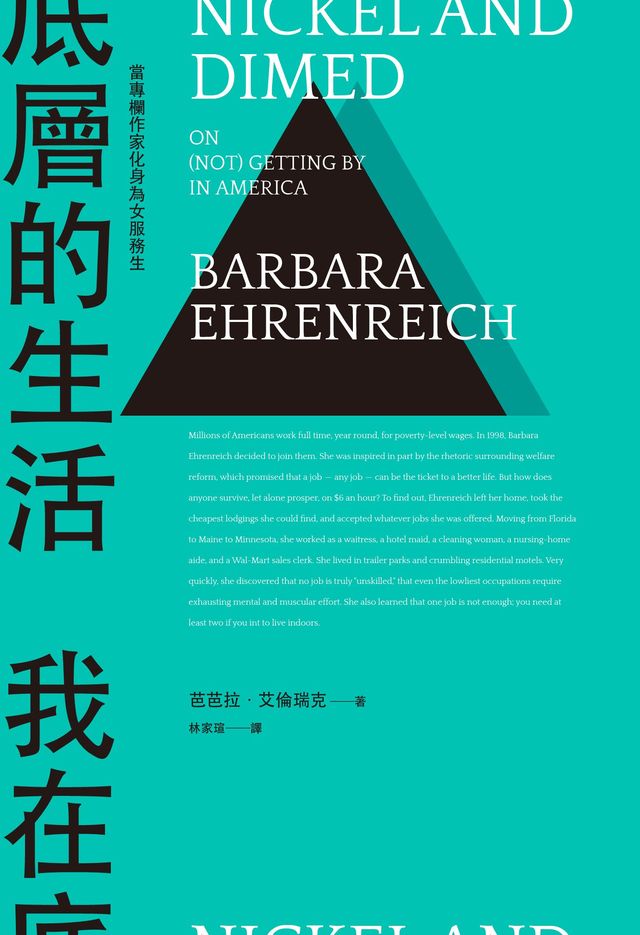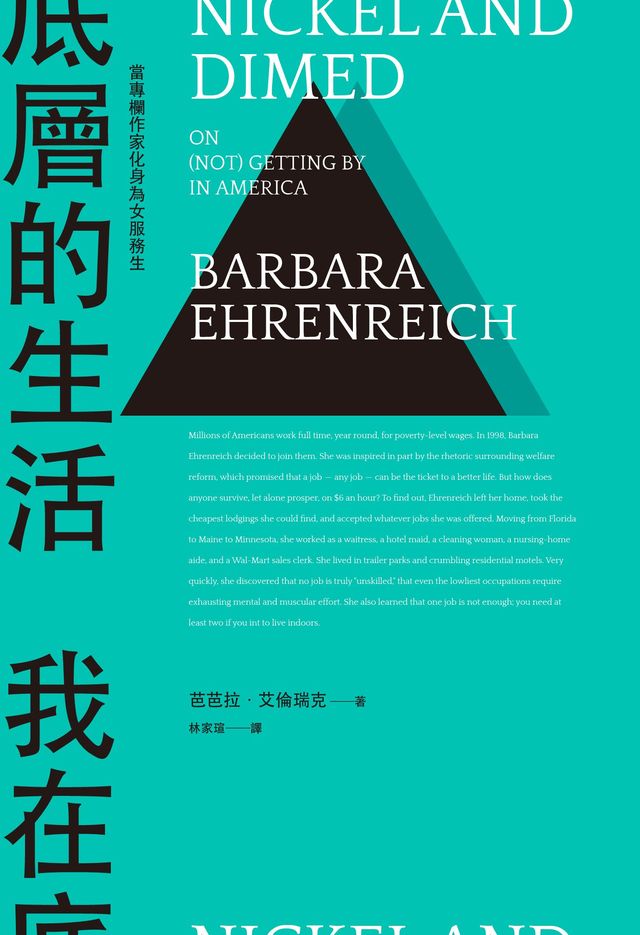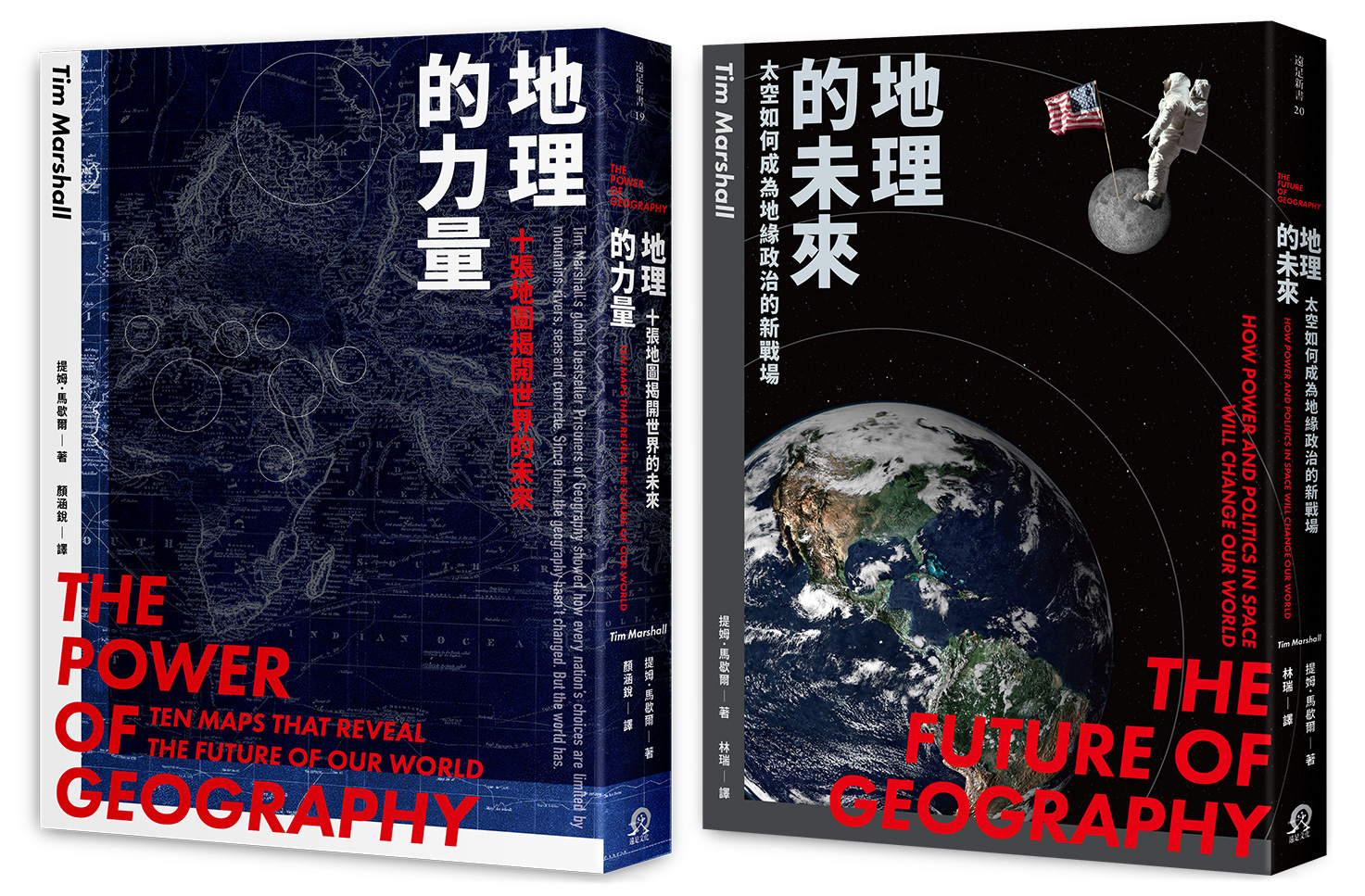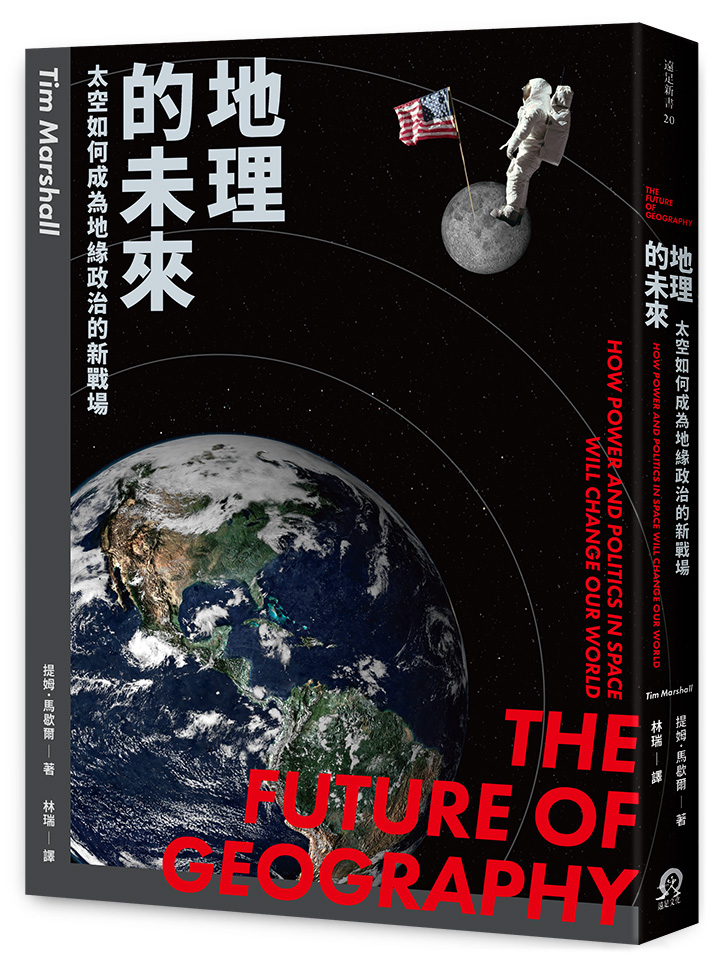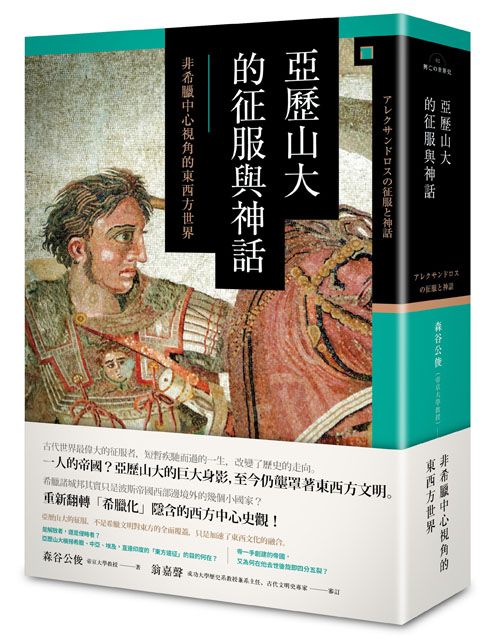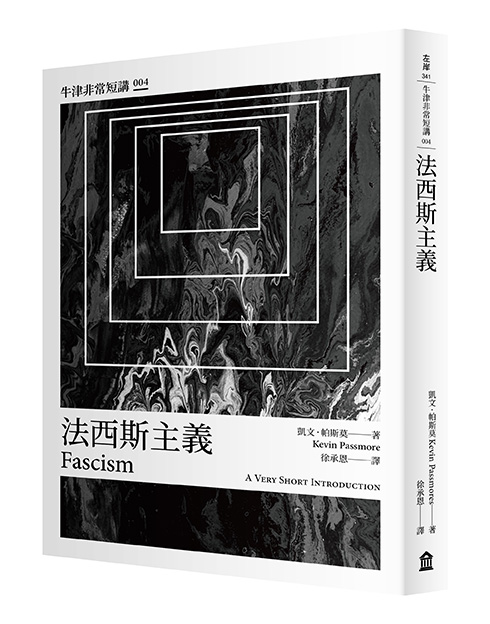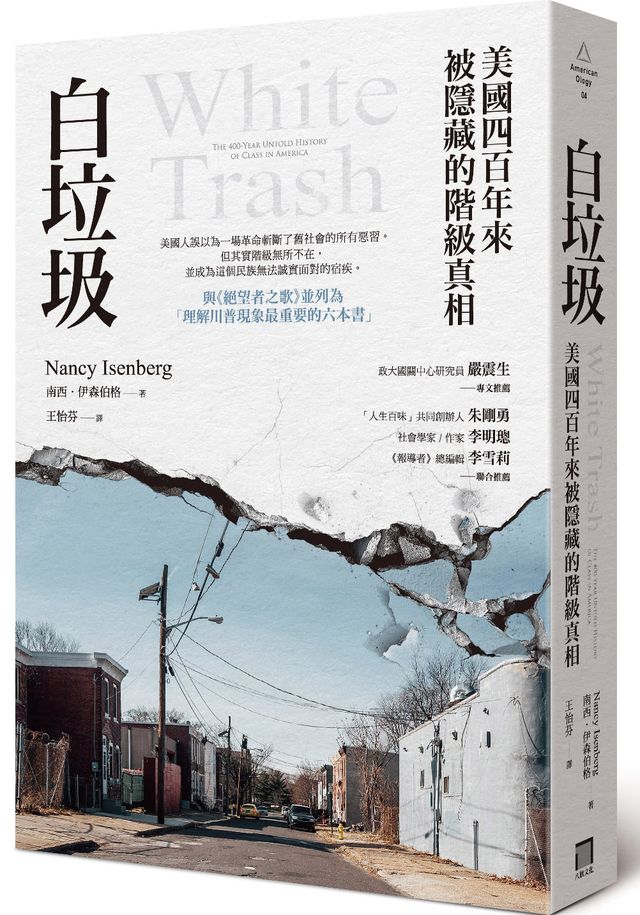開啟「臥底報導」先聲、探討「窮忙族」代表作
猜猜看,餐廳女服務生、旅館房務員、鐘點清潔工、看護之家助手,和沃爾瑪的售貨員,哪一種低薪工作最磨人心志、把人逼近發狂崩潰的臨界點?
本身並不貧窮的人往往想像貧窮是一種過得下去的生活。
儘管很清苦,但窮人們總是想出辦法活下來了,不是嗎?他們「總是在那裡」。並不貧窮的人很難理解那其實是一種極度痛苦的狀況:午餐可能只有一包多力多滋,所以早在下班之前就已經餓得快要暈倒;所謂的「家」就是一輛可以窩著睡覺的廂型車;即使生病或受傷,還是得咬緊牙關「用工作撐過去」,因為根本沒有生病津貼或健康保險,而只要一天沒有薪水,就意味著隔天連幾塊錢的伙食費都付不出來。這些經驗根本不能被歸類為「過得下去」,而是一種經年遭到剝削、受到無情懲罰的生活方式。
我們從小就被教導「努力工作是成功之道」、「努力工作就會出人頭地」,或是「我們就是努力工作才有今天」。我們被灌輸「努力工作」是脫離貧窮的不二法門,沒有人告訴我們,就算你「努力工作」(努力到你甚至從來沒想像過的程度),還是有可能發現自己仍然深陷在貧窮和負債中,甚至越陷越深。我們可能會發現,「再怎麼努力工作都沒有用」才是我們需要面對的真實世界。
為什麼會這樣?芭芭拉‧艾倫瑞克決定親自加入他們,找出答案。「如果你想了解一個階級,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他們!」
芭芭拉頂著60歲的身軀,從佛羅里達到緬因,再到明尼蘇達;她當了女服務生、旅館房務員、鐘點清潔工、看護之家助手,以及沃爾瑪的售貨員。她秉持著科學精神,梳理出低薪工作生存下去的方式:任何工作都需要技巧,不論它有多基本;最底層的工作,也要求精神和體力上的龐大付出;以及,如果想要有個安穩的小窩,你至少需要兩份工作。
這本書並不是關於什麼出生入死的「臥底」冒險經驗。她做的事幾乎任何人都做得來:找到工作,把這些工作做好,努力量入為出使收支平衡。事實上,這正是幾百萬名美國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她以一貫的幽默與辛辣描寫這段交雜著汗水、淚水、清潔劑與番茄醬的低薪生活。她把苦日子寫得深刻,也興味盎然。
有人會說只要懂得設身處地,這些狀況並不難想像。當然。只是,每個人對忙碌的定義不一樣;對貧窮也是。如果少了這些作品,或許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關在象牙塔裡的想像,距離現實多遠。金融風暴後,窮忙族成為普遍現象,本書也成為探討「窮忙族」的代表作品。
名人推薦
貧困者和決策者,那些擁有話語權的人們,居住在同一個國家,卻是兩個世界,後者擁有光環,提出的意見有人重視,而前者無人聞問,連真實的困境都被忽略,「反正一直都有窮人嘛」。芭芭拉的「降世」正是為了讓更多人知道,原來有這樣一個「在職貧窮」的事業和階級存在。──林立青
這些經驗的描述令人難以忘懷,她的文筆生動、機智,很少讀者能不被美國經濟底層那種令人羞愧的現實狀況觸動。本書必定將在底層報導的經典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新富餘》作者,茱麗葉‧修爾(Juliet Schor)
美國對於經濟繁榮的負面視而不見。艾倫瑞克巧妙地層層剝除我們的自我否認,試圖消除富人和窮人、被服侍者和服侍者的區分。這本勇敢而坦誠的書是一項挑戰,挑戰我們是否能創造出一個不如此嚴重分化的社會。──《震撼主義》作者,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 1941~)
洛克菲勒大學細胞生物學博士,曾任《時代雜誌》專欄作家,作品也常出現在《哈潑》、《國家》、《新共和》等刊物,是相當活躍的女性主義者與民主社會主義者。她出身礦工家庭,讀大學時受到反戰運動啟蒙,拿到博士學位後決定放棄教職,投入寫作與社會運動;也因為前夫是卡車司機,特別關注美國社會底層(M型另一邊)的生活。《我在底層的生活》出版後,她被診斷罹患乳癌,在治療過程中以此個人經驗探討美國的醫藥產業問題。艾倫瑞克至今已出版二十一本著作,包括暢銷作品《我在底層的生活》、《失業白領的職場漂流》、《失控的正向思考》、《嘉年華的誕生》,以及自傳作品《我的失序人生》,最新作品為《Natural Causes: An Epidemic of Wellness, the Certainty of Dying, and Our Illusion of Control》。
林家瑄
清大外語研究所畢業。譯有《兩位嚴肅的女人》、《我的失序人生》等專書及文章。
就跟我下修的生活條件一樣,一種新型態的醜惡也出現在傑瑞餐廳裡。首先,我們是透過用來輸入點餐內容的電腦螢幕告示才得知,從今以後有個新規定:旅館附屬的酒吧禁止餐廳員工進入。我透過祕密情報網得知,肇事者是那位訓練我的超能幹二十三歲女生。她其實也住在拖車屋,而且是三個小孩的媽。有天早上不知道什麼事情使她失控了,所以她溜出去喝口酒,結果神智不清地回來。這項禁令對愛倫造成的傷害最大,因為她習慣在下班後解開一直被橡皮筋綁得緊緊的頭髮,到旅館酒吧裡喝幾杯便宜琴酒再回家。我們其他所有人也都感受到這項禁令帶來的壓力。就在隔天,當我要進乾貨儲藏室拿吸管的時候,發現門是鎖著的。這道門以前從來沒鎖過,我們整天都要進進出出,拿紙巾、果凍盒及外帶用的保麗龍杯。魁梧的協理維克過來替我開門,他跟我說,他抓到一個洗碗工想從裡面偷東西,而且很不幸地,那個惡棍得一直跟我們待在一起,直到代替的人來為止,所以他把門鎖起來。我當時忘了問他,那人到底想偷什麼,但維克告訴我那個人是誰:理平頭戴耳環的小伙子,妳知道,他現在就在門後。
我希望我可以跟各位說,我當時立刻衝回去問喬治,了解他那邊的說法是什麼。我希望我可以跟各位說,我起而對抗維克,堅持替喬治找一名翻譯,讓他能為自己辯白,或宣稱我會找到願意義務處理這個案件的律師。最起碼,我應該要作證說明這孩子很誠實。我想不通的是,乾貨儲藏室裡根本沒有什麼值得偷的東西,至少沒有半樣值得在黑市買賣的東西:「我是喬治啦,我手上有兩百包……也許兩百五十包的小番茄醬。你要不要買?」我的猜想是,就算喬治真的有拿什麼東西,也只會是一些鹹餅乾或一罐櫻桃派配料粉,而且動機只是因為飢餓。
所以,為什麼我沒有插手干預?絕對不是出於所謂記者的公平客觀,那往往是在掩蓋背後的道德麻痺。相反地,某種新的、令人作嘔的、奴性的東西感染了我,就跟晚上下班終於能脫下衣服時,我還能從內衣上聞到的那股廚房怪味一樣。在真實生活裡,我算是有一點點勇敢,但許多勇敢的人在戰俘營裡被淘空了勇氣,而也許,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整體環境有如戰俘營的美國低薪工作場所。也許,在傑瑞餐廳待上一個月或更久之後,我可能會重獲我的十字軍精神。但也有可能在一、兩個月後,我會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說不定就是變成一個會把喬治出賣的人。
但這並不是當時我火燒眉毛要解決的事。跳入貧窮生活一個月之後,我終於找到夢寐以求的工作:房務人員。因為我去了唯一可能對我的能力有點信心的地方:傑瑞餐廳從屬的旅館。我到人事辦公室裡,急切地吐露我的狀況:我必須找第二份工作,否則就付不出房租;還有,不,我不能當櫃檯接待員。「好吧,」人事室的小姐不耐煩地說:「那妳就當房務員。」之後就趕我去找房務經理米莉。她是個瘦小而神經質的西班牙女子,叫我「寶貝」,然後遞給我一本小手冊,內容強調員工必須有積極的態度。時薪是六點一美金,工作時間從早上九點開始,直到「能完成工作的時間」為止,我希望這是指下午兩點之前。看到負責帶我的中年非裔美國人卡蘿塔之後,我就知道根本不必開口問有沒有健保。因為這位要我叫她卡莉的女子,前排上方的牙齒已經完全掉光了。
我當房務員的第一天,也是我這一生在西嶼過低薪生活的最後一天,雖然我當時並不知道這點。那一天,卡莉的心情很糟。我們被分配要打掃十九個房間,大部分都是「退房」而非「續住」,退房的房間要進行全套清潔整理,包括換床單、吸塵以及擦洗浴室等。當我們發現其中一個原本被列為續住的房間結果卻是退房時,卡莉打電話向米莉抱怨,但當然毫無用處。「那就把這個該死的王八蛋弄好。」她命令我道,於是我負責弄床鋪,她在浴室噴噴擦擦。一連四小時我不曾休息。我把床單褪下來,再重新鋪床,每張大床平均花四分鐘半,我是可以加快到三分鐘,但看不出有必要這麼做。我們用手把較大的灰塵髒物撿起來,試圖減少使用吸塵器的機會,但大多數時候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努力把重達三十磅的巨大吸塵器拽下清潔車,費力地把它在地板上拖來拖去。有時候卡莉會遞給我一個噴瓶,上面的標籤寫著BAM(實際上,那是幾個字的縮寫,第一個字不祥地以「丁酸」[Butyric]開始,但其他的字已經磨損得看不見了),然後她就讓我清理浴室。在這裡,可沒有服務生面對客人的責任感能激勵我,我只能全神貫注把浴缸裡的陰毛撿乾淨,至少是我能看得到的暗色系毛髮。
清潔續住房間的時候,我原本滿期待那種私闖別人空間的感覺,以為有機會檢視陌生人祕密的一面。但這些房間裡總是乏善可陳,而且整潔到令人訝異:拉鍊袋裝的刮鬍刀組、整齊地貼牆放置的鞋子(房間裡沒有衣櫃)、浮潛之旅的宣傳單、最多再加上一、兩個空酒瓶。使我們能一直工作下去的是電視,播放的節目從傑瑞.斯布林格秀(Jerry Springer Show)、莎莉.拉菲爾秀(Sally Raphael Show),再到檀島騎警(Hawaii Five-O),最後則是肥皂劇。若電視上出現特別有趣的東西,比如傑瑞秀著名的那句「我們可不接受『不』這個答案」,我們就在床沿坐下來咯咯笑一會兒,彷彿我們正在開睡衣派對,而不是在做一份毫無出路的工作。肥皂劇是最棒的部分,卡莉會把音量調到最大,這樣她在清潔浴室或開著吸塵器的時候也不會錯過任何對白。在五○三號房的時候,瑪西雅質問傑夫跟蘿倫的關係;在五○五號房的時候,蘿倫冷酷地嘲笑丈夫外遇的可憐瑪西雅;在五一一號房的時候,海倫要給亞曼達一萬美金,條件是亞曼達不能再見艾瑞克,這段對話使卡莉從浴室裡走出來,仔細瞧著亞曼達困惑的臉。「當然要拿,小姐。」她忠告道:「我就一定會拿。」
不久之後,我們所打掃的觀光客房間,開始漸漸跟肥皂劇裡的高級裝潢融合在一起。我們進入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裡只有舒適可言,每天都是放假日,只等著被浪漫的邂逅填滿。然而在這個夢幻世界裡,我們只是兩個闖入者,被迫要為自己的出現付出代價—背痛和永遠只能乾瞪眼的份兒。旅館裡有太多鏡子,不斷映照出一個身影,樣子就像推著破舊超市購物車在馬路上蹣跚前進的人:邋遢,穿著大了兩號的潮濕旅館馬球衫,汗從下巴淌下來,宛如口水一般。當卡莉宣布休息半小時吃午餐的時候,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這時才發現,原來她一直放在清潔車上的那袋乾癟熱狗捲,並不是某位退房客人留下的垃圾,而是她的午餐。頓時,我自己也吃不太下了。
由於有電視,再加上身為第一天上班的新人,我沒有什麼資格打開話題,因此我對卡莉所知不多,只曉得她身上很多地方都在痛。工作時她都慢慢移動,低聲抱怨著關節痛之類的,但這點也許會使她失去工作。因為年輕的外籍房務人員(來自波蘭和薩爾瓦多)都會在下午兩點把房間打掃完,而卡莉則拖到六點才做完。她說,反正我們是領時薪的,實在沒必要這麼急。然而管理階層已經僱來一名女子,進行工作效率評估之類的工作,而且據說以後可能會改成以打掃的房間數來計算薪水。她也對於種種不尊重她的小動作感到耿耿於懷,而且不只是管理階層這麼對待她。「他們壓根兒不在乎我們。」她如此形容旅館住客;事實上,他們根本沒注意到我們的存在,除非房間裡有東西被偷了,「這會兒他們可不會放過妳。」我們並肩坐在休息室吃午餐,一名身穿維修人員制服的白人男子走過,卡莉出聲叫他。「嘿,」她語氣很友善:「你叫什麼名字?」
「彼得潘。」他說,人已經背向我們走開。
「這一點都不好笑。」卡莉說,她轉頭看我。「那根本不算回答,為什麼他要開這種玩笑?」我大膽回答說他是在擺架子,於是她點點頭,彷彿這是醫生做的診斷:「對,他是在擺架子。」
「也許他今天很不順。」我繼續多說點,但並不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替白種人辯護,而是從她扭曲的表情可以看出她有多受傷。
我在下午三點半要求下班,此時另一名房務人員對我提出忠告,到目前為止,從來沒人能一面在傑瑞餐廳當服務生一面還當房務員,「一個小伙子曾有一次成功做了五天,而妳已經不是小伙子了。」我把這項有幫助的資訊記在心裡,然後衝回第四十六號拖車屋。我吞下四顆布洛芬(Advil,這次的止痛藥名),沖澡,彎著身體擠進淋浴間,努力讓自己穩定下來,迎戰即將來臨的另一輪工作。這大概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的再生產」,意思是,一名勞工得做一些事情讓她能再度進行勞動。雖然我想一氣呵成地從一個工作轉換到另一個,傑瑞餐廳規定要穿的那條褲子卻成了意外阻礙。昨晚我用手搓洗夏威夷衫的時候,那件褲子在四十瓦的燈泡下看起來還過得去,但在白天的陽光下,我才發現它上面都是沙拉醬弄的汙漬。結果兩份工作之間大約一小時的休息時間裡,我幾乎都在試圖用海綿除去褲子上的食物斑,然後把褲子攤在車子引擎蓋上曬乾。
若我能灌下足夠的咖啡,又不對喬治越來越糟的狀況耿耿於懷,理論上我應該能同時做好這兩份工作。被懷疑偷竊之後的頭幾天,喬治似乎並不明白自己惹上了什麼麻煩,我們快活的會話課仍持續進行。但他最近來上班都顯得無精打采,鬍子也沒刮。跟我擔心的一樣,今晚他看起來更像鬼魂,眼睛底下掛著兩個深深的黑眼圈。有那麼一刻,我因為必須把配烤馬鈴薯的酸奶油醬裝在一些小紙杯裡,而暫時站著沒跑來跑去,他於是走上前,顯然很想努力用有限的字彙跟我談一下,可是我卻在這個時候被叫去外場負責一張桌子。我當場決定,今晚我賺到的小費全都給他,管它什麼低薪生活實驗的省錢原則。八點的時候,愛倫和我一起站在廚房裡臭得要命的角落囫圇吞幾塊點心,但我只來得及吃下兩、三根義大利乾酪棒,而午餐我只吃了幾塊麥克雞塊而已。我告訴自己,我一點都不累,但也許「我」只是連感覺累的力氣都沒了。若我對整個情況更有所警覺的話,就會看到毀滅的力量已經朝我逼近。餐廳裡只有一名年輕廚師當班,名叫「耶穌」(請用法文腔念),而他才剛接這份工作。另外還有喬伊,我們工作到一半她才出現,腳上穿著高跟鞋,身穿一件緊貼身體曲線的白色洋裝,氣得七竅生煙,顯然剛從某個雞尾酒吧被硬叫過來。
然後,巨大的人潮來襲。我負責的桌子有四張立即客滿。如今四張桌子的客人對我來說不算什麼,但前提是他們大發慈悲,別在同一時間進餐廳。當我去服務二十七桌時,二十四、二十五及二十八桌的客人都嫉妒地看著。當我服務二十五桌的時候,二十四桌的客人則對我怒目而視,因為還沒人去幫他們點菜。二十八桌是四個雅痞型的客人,意思是每一樣菜他們都有意見,連雞肉凱撒沙拉都要另外指示。坐在二十五桌的是一對中年黑人夫婦,他們抱怨冰茶不新鮮、桌面黏黏的,雖然這些抱怨其實不無道理。但二十四桌的客人才真是海嘯級的:十名英國觀光客,他們似乎下定決心要完全透過嘴巴來吸收美國經驗。每個人都至少點兩份飲料:冰茶和牛奶雪客,麥格(Michelob)啤酒和水(請在水裡加上檸檬片),還有數量龐大、種類繁雜的食物:早餐特餐、義大利乾酪棒、雞肉條、墨西哥薄餅,要起司和不要起司的漢堡,配料是薯餅,要加切達起司、加洋蔥、加肉汁,還要調味炸薯條、原味炸薯條、香蕉片。耶穌累慘了!我也是!當我終於端著他們的第一波食物抵達時(在此之前因為要幫他們加點,我又跑了三趟),其中一個大概自以為是黛安娜王妃的女人,竟然拒絕把雞肉條跟鬆餅及香腸特餐一起吃,因為她現在才說,她點雞肉條是要當作前菜。其他人原本會接受眼前的食物,但已經在喝第三杯啤酒的黛安娜王妃卻堅持,他們在吃前菜的時候,其他食物都要端回廚房去。同時,那些雅痞正召我過去幫他們添更多無咖啡因咖啡,而那對黑人夫婦看起來就像隨時要叫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的人來抗議一樣。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大多淹沒在一片戰雲中。耶穌開始撐不住了,他面前的小印表機吐出點餐單的速度比他把單子撕下來的速度還快,更別談趕得上進度出餐了。一種逼人的躁動不安開始從客人之間升起,而所有的桌子都坐滿客人。就連堅不可摧的愛倫都因壓力顯得臉色蒼白。我把二十四桌重新加熱的主菜拿去,他們立刻要我退回廚房,理由不是微波得太冷就是太硬。當我帶著他們的托盤回到廚房時(一次拿三個托盤,連跑三趟),喬伊雙手叉腰等在那裡質問我:「這是什麼?」她的意思是指食物:好幾盤被退回的煎餅、各種口味的炸薯餅、土司、漢堡、香腸、蛋。「呃,切達起司炒蛋,」我試著回答:「而那是──」「不對,」她對著我的臉尖叫:「它是傳統炒蛋,巨無霸炒蛋,還是特製炒蛋?」我假裝研究菜單找尋線索,但混亂的程度已經達到頂峰,不只那些餐盤如此,我的腦袋也一樣。而且我得承認,我已經根本想不起原始的點餐內容了。「妳不知道特製炒蛋跟傳統炒蛋的差別?」她狂怒地逼問我。事實上,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的雙腿已經沒興趣再繼續支持下去,它們大喊著要彎下來。我被一名雅痞給救了(老天慈悲,不是我負責那桌的雅痞們),因為他選擇在這一刻衝進廚房裡,大吼他點的食物已經過了二十五分鐘還沒來。喬伊尖叫著請他滾出她的廚房,接著暴怒地朝耶穌發火,順便還把一個空托盤扔過廚房表達她的憤怒。
我離開了。我沒有大喊「我不幹了!」,就只是離開。我沒有完成分內的雜項工作,也沒有從收銀櫃檯那裡拿走我的小費(如果有的話),更沒有要求喬伊允許我走。而令人驚訝的是,我真的可以不經允許就走出去,門會打開,厚重的熱帶夜晚空氣會散開來讓我過去,我的車也仍然停在先前停的地方。走出餐廳,我沒有沉冤得雪的感覺,也沒有罵了「去你的!」之後的爽快,只有令人招架不住的沉重失敗感籠罩我和整個停車場。我帶著科學精神開始從事這項實驗,以為它就像一道數學命題,但在實驗的過程中,太長時間工作、太需要不計一切專注在眼前事情上,使我不知不覺變成一個眼界狹窄的人。這場實驗變成對我的試煉,而顯然我沒通過。我不只沒能力身兼房務人員和服務員,也忘了把小費給喬治。對此我感到很難過,像蓋兒和愛倫這種辛勤工作又慷慨的人,一定能了解其中緣由。我並沒有大哭,但多年來我第一次發現,我的淚腺還在,而且仍然有實力發揮它的功能。
***
我搬出拖車屋公園的時候,把四十六號拖車屋的鑰匙交給了蓋兒,並設法把我的押金轉給她。她告訴我,瓊安還住在她的廂型車裡,而史都已經被爐邊餐廳開除了。根據最新傳聞指出,他透過餐廳電話訂的毒品是快克,而且他被抓到偷收銀機裡的錢來付帳。我一直沒打聽到後來喬治怎麼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