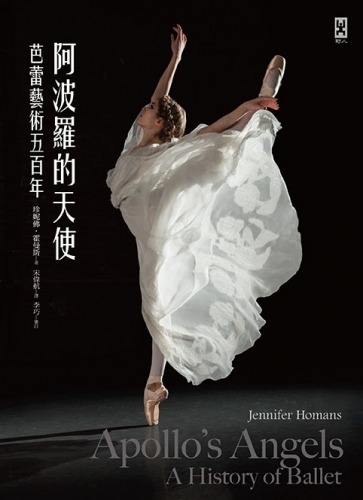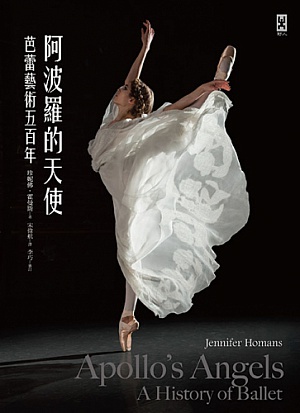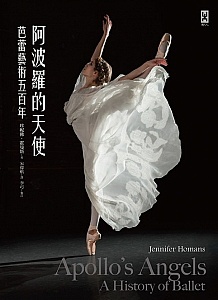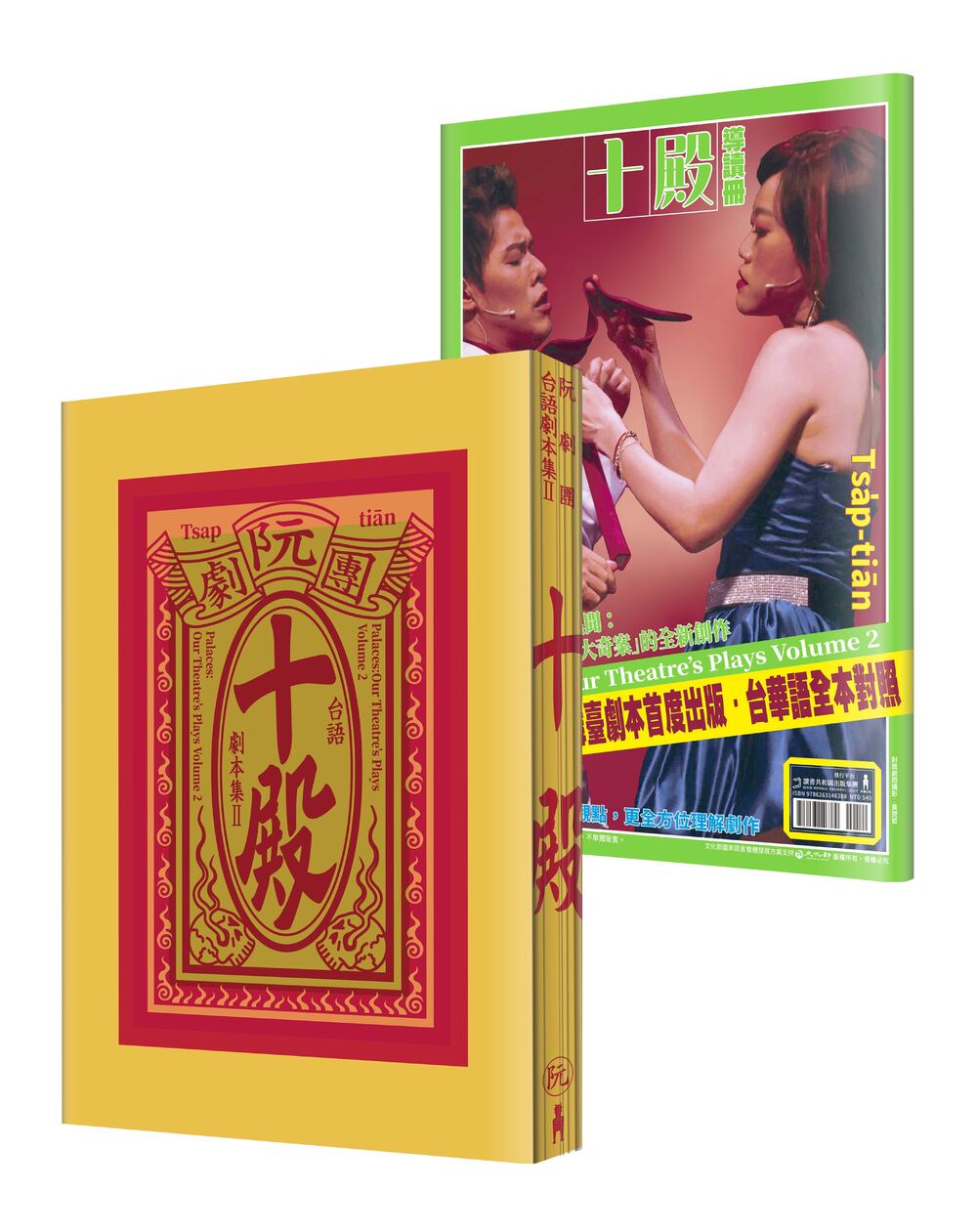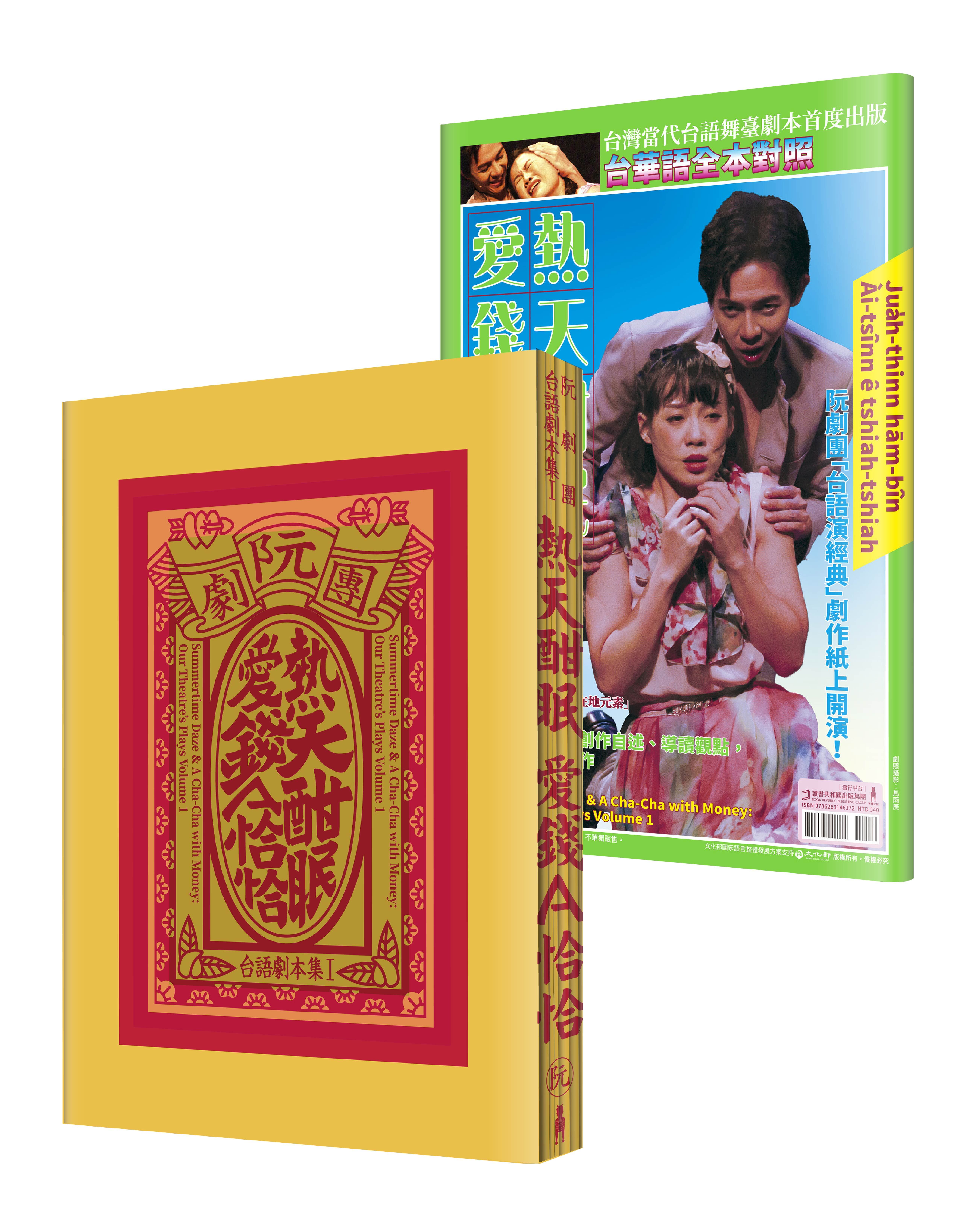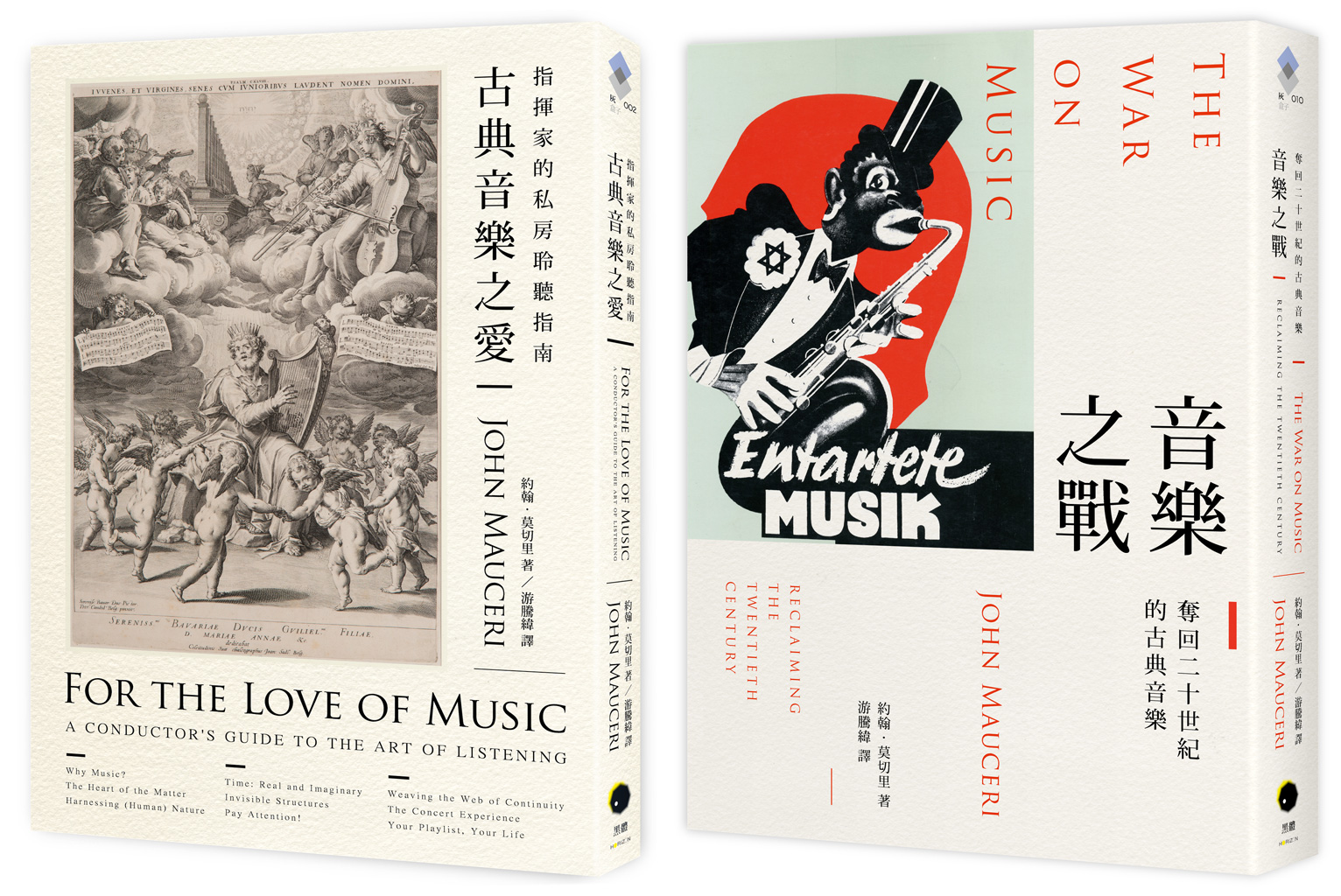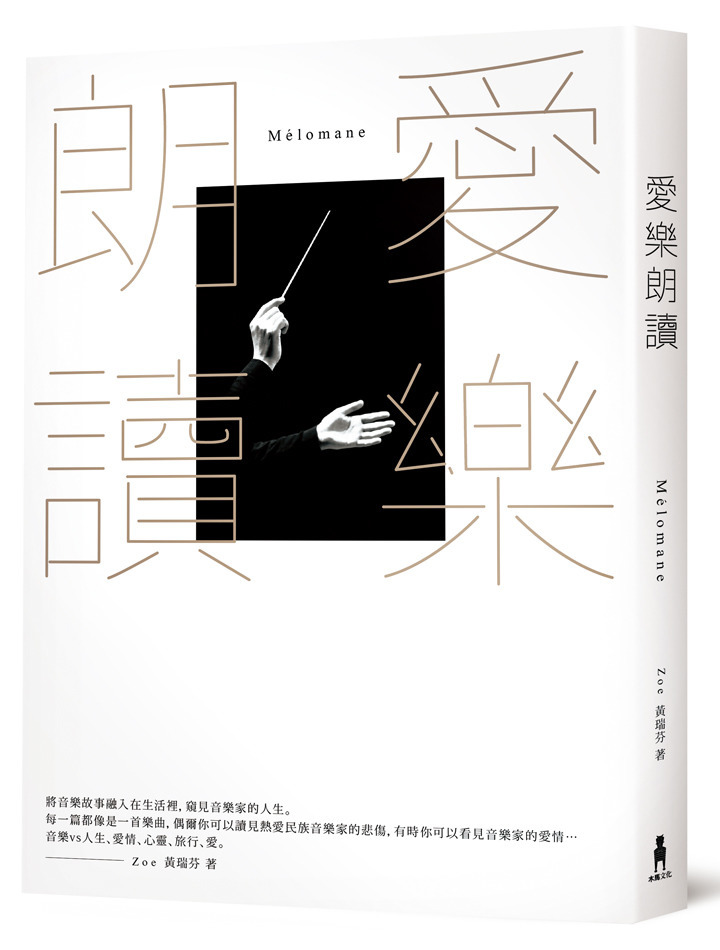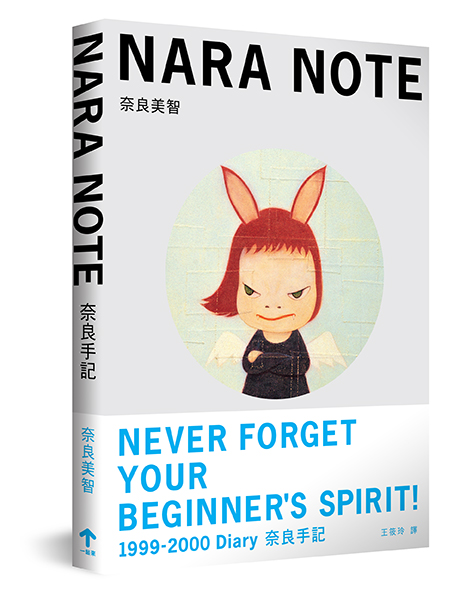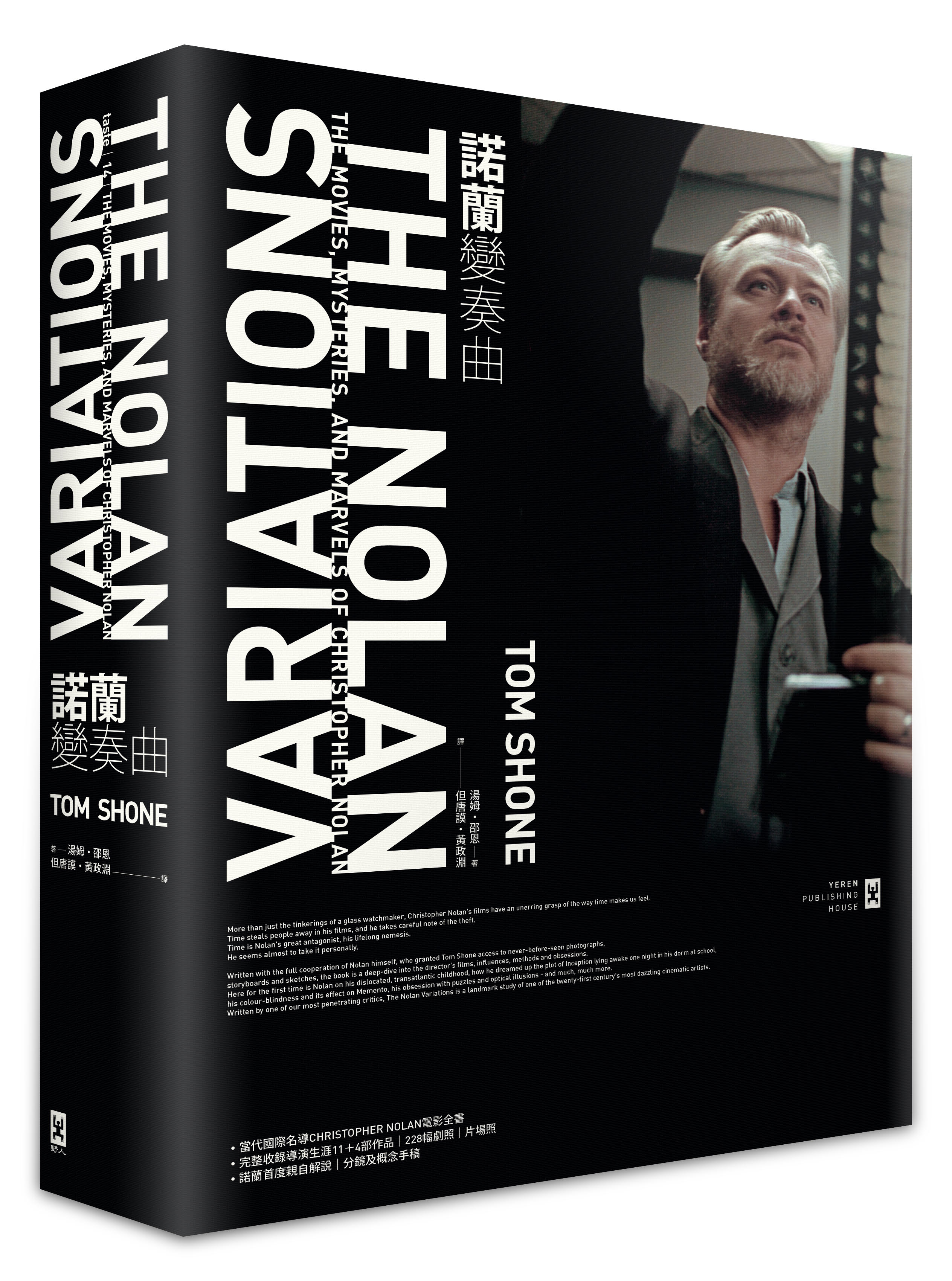導言 名家和傳統
我的父母都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所以,我是在學術氣味濃厚的環境長大的。我不曉得當初我母親送我去學跳舞究竟是為了什麼,只知我母親愛看表演。說不定依她出身美國南方、注重禮節儀態的性子,芭蕾正合她的脾胃;而我家那一帶,也正好開了一所舞蹈學校,我母親自然送我過去學舞。那所舞蹈學校是一對老夫婦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有好幾支俄羅斯人的芭蕾舞團來到美國各地巡迴演出,他們便在其中一支舞團跳舞,順勢就留在美國。不過,老夫婦開的舞蹈學校跟一般常見的不同;沒有一年一度的《胡桃鉗》成果發表會,也看不到粉紅色的短蓬蓬裙和粉紅色的舞襪。老先生還罹患「多發性硬化症」,只能坐輪椅教課。所以,但見教室裡的他,耐著性子,強壓下火氣,用複雜難懂的辭彙詳述口令,學生則由老太太帶領,賣力做出老先生要的動作。芭蕾雖然也是人生的一大樂事──這一點,老先生當然不會略過──不過,芭蕾之於老先生,更是極其嚴肅的人生大事,不可等閒視之。
不過,將我帶進職業舞者一途的老師,卻是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博士的一名研究生。他以前當過職業舞者,我便是由他帶領,方才領悟芭蕾的一整套動作組成之精密、複雜不下於任何語言。芭蕾一如拉丁文或古希臘文,有其規則,有其詞性變化,有其詞尾變化。不止,舞蹈的法則更不是隨隨便便就訂下來的;舞蹈的法則一樣要符合自然律。跳得「對」,不是由誰的看法或喜好在指揮的。芭蕾也算是一門「硬科學」(hard science),有實際存在的物理現象作憑證。芭蕾另也富含感受和情緒,隨音樂和動作自然流瀉,扣人心弦。芭蕾還像默讀,有幸毋須出聲即可表情達意。不過,萬事俱備、配合無間之時,芭蕾洋溢的超脫欣快之感,說不定更是無與倫比。斯時,動作的協調和音樂的感受搭配天衣無縫,肌肉的爆發力和掌握節奏的技巧同聲相契──至此,人身便是一切的主宰。這時,「我」,就可以放手不管。而「放手不管」之於舞蹈,像是萬事皆休:大腦,軀體,心靈,一概放下,無所罣礙。我想,也就是因此,才有那麼多舞者都說,儘管芭蕾規矩多、限制多,舞動之際,卻像掙脫自我的束縛──澈底自由!
而接下來我又再有幸管窺芭蕾的奧妙,便是得力於喬治.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 1904-1983)於紐約創立的「美國芭蕾學校」(School of American Ballet)。我在那裡師事的前輩,全都是俄國人,全都是出身另一年代、另一國度、丰姿萬千的芭蕾伶娜。菲莉雅.杜布蘿芙絲卡,十九世紀末生於俄國,「俄國大革命」(Russian Revolution, 1917)之前在帝俄首都聖彼得堡的「馬林斯基劇場」(Maryinsky﹝Mariinsky﹞ Theater)芭蕾舞團跳舞。後來加入歐洲的「俄羅斯芭蕾舞團」(Ballets Russes),最後落腳美國紐約,以教舞維生。只是,我們學生都看得出來,她身上有一部分始終留在別的地方,留在離我們很遠、很遠的世界。她全身上下怎麼看,就是跟別人不一樣。濃妝,長長的假睫毛,氣味甜膩的香水。我記得她總是一身華麗的珠寶,深濃的藍紫色緊身舞衣搭配同色系的圍巾,雪紡裙外加粉紅色的舞襪;一雙非比尋常的修長美腿依然結實矯健,驚鴻一瞥,永世難忘。就算沒在跳舞,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無不雍容透著華貴,優雅的儀態遠非美國少女所能企及於萬一。
此外還有:妙麗兒.史都華,英國舞者,有幸和安娜.帕芙洛娃(Anna Povlova, 1881-1931)同台共舞;安東妮娜.屯科夫斯基和海倫.杜汀,兩人都出身基輔(Kiev),也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移民美國。杜汀還瘸了雙腿,據說是在蘇聯被打斷的。不過,丰華最為耀眼的,或許還是首推雅麗珊德拉.丹尼洛娃。她於一九二四年和巴蘭欽一起從列寧格勒出亡。丹尼洛娃和杜布蘿芙絲卡很像,都曾是帝俄時代的舞者,都愛粉彩的雪紡紗,都戴蜘蛛腳一樣的特長假睫毛,都搽很濃的香水。她在俄國是父母早早雙亡的孤女,我們這些學生卻人人深信她系出貴冑名門,片刻也不曾懷疑。我們的儀態、我們的舉止,由她負責指導,不僅限於舞蹈課,日常生活也在內──不要穿T恤!不要彎腰駝背!不要吃路邊攤!她諄諄告誡我們:舞者所學、所選的行當,就是與常人不同;舞者的樣子,就是要和「其他人」不一樣。這些話,當時在我覺得十分正常,卻也十分怪異。說是「正常」,是因為我知道我們這些老師都是名家,傳授的一定是很重要的學問。而且,站得筆直,行動優雅,專心致志奉獻於舞蹈,不管怎樣,確實襯得我們和其他人不太一樣。我們真的像是「天之驕子」,或,自以為是「天之驕子」吧。
不過,感覺卻還是很怪:沒有誰會好好把其中的道理講給你聽,教學法都很專橫,專橫到很討厭。在他們面前,我們作學生的本分就只在模倣、吸收,尤其要乖乖聽話。我們這些俄國老師講話再客氣,也只擠得出「麻煩你」幾個字。一聽有人問起「為什麼」,不是輕蔑苦笑,就是乾脆當作耳邊風。我們還不准到別的地方學舞(有的規定我們這些學生還是懶得去管,這一條便是)。這樣的作風在那時候實在格格不入。我們都是一九六○年代長大的孩子,聽人滿嘴權威、責任、忠誠,感覺像是遇到了天大的老古板,時地一概不宜。只是,我對這些俄國老師教的東西興趣太濃,捨不得放棄或是跑掉。最後,學了多年,看了多年,終於領悟我們這些老師不僅在教舞步,不僅在傳授舞蹈的技法。其實,他們也在向我們傳授他們身負的文化和傳統。「為什麼」,根本不是重點。舞步不僅是舞步。他們的人生、他們的呼吸,都是活生生的明證,展現的是(在我們看來)失落的過去──不僅關乎他們的舞蹈,也關乎他們身為舞蹈家、他們所屬的民族心中常懷的信念。
而芭蕾也不像是我們這紅塵俗世所有。以前我會(和我母親)排隊去看「波修瓦」(Bolshoi)、「基洛夫」(Kirov)芭蕾舞團的演出,跑到「大都會歌劇院」跟大家擠在水洩不通的站位席最後面,伸長脖子看「美國芭蕾舞團」(American Ballet Theatre)和米海伊爾.巴瑞辛尼可夫(Mikhail Baryshnikov, 1948-),或是擠在教室看魯道夫.紐瑞耶夫(Rudolf Nureyev, 1938-1993)示範芭蕾把杆練習。不僅芭蕾。那時候的紐約是舞蹈的活力中樞,什麼都看得到,什麼都學得到: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 1894-1991)、摩斯.康寧漢(Merce Cunningham, 1919-2009).保羅.泰勒(Paul Taylor, 1930-);爵士舞、佛朗明哥、踢踏舞;市中心還有小型實驗舞團在工作坊、倉庫演出。但在我,跳舞的首要理由,僅此唯一:「紐約市立芭蕾舞團」(New York City Ballet)。那時,巴蘭欽開疆拓土的舞蹈生涯已近蓋棺論定,所帶的舞團以藝術和知性的活力,在在震撼眾人耳目。我們學芭蕾的人,也都知道巴蘭欽在做的事很重要,從來未曾質疑過芭蕾凌駕一切的地位。所以,芭蕾才不會老;芭蕾才不「古典」;芭蕾才沒過時。還相反,舞蹈蓬勃的活力遠甚於以往;所展現者,遠非我們所知、所能想像。舞蹈填滿我們的日常生活,不管什麼舞步、風格都要拿來分析,不管什麼規則、作法都要拿來辯論。我們對舞蹈的熱忱,直逼宗教信仰。
接下來幾年,我轉為職業舞者,追隨過好幾支舞團和編舞家,也發現舞蹈王國不是只有俄國人而已。我和丹麥舞者共事、同台演出,也和法國、義大利舞者一起粉墨登台,還試過古義大利派芭蕾名師發明的「切凱蒂教學法」(Cecchetti method),一度企圖拆解英國「皇家舞蹈學院」(Royal Academy of Dance)制訂的複雜課程。至於俄國舞者,這時期也不再局限於先前認識的那些老師而已。蘇聯舞者的技法,和杜布蘿芙絲卡那一輩的帝俄舞者南轅北轍。所以,情況就變得很妙了:芭蕾的語彙和技法看起來十全十美、普世通用,各國的派別卻又各自分立,獨樹一幟。例如美國這邊由巴蘭欽教出來的舞者,做「阿拉伯姿」(arabesque)的時候,臀部會跟著腿部上揚,也愛利用旋轉來加強速度,強調延伸和跳躍的線條。英國舞者看了可會面如土色,覺得這樣的旋轉「不雅」;英國舞者偏好含蓄內歛的風格。丹麥舞者則以乾淨、俐落的足下工夫(footwork)和敏捷、輕盈的跳躍見長。這和他們跳舞的重心是放在腳掌的前半部,腳步不會拖泥帶水有部分關係。但是,腳跟不放下來,就永遠做不到蘇聯舞者特有的優雅飛躍和彈跳。
此間的差別,不僅在美感而已:感覺就是不會一樣。舞者選擇這樣子跳而不那樣子跳,當下,就會像是變了個人。《天鵝湖》和《競技》(Agon)同為芭蕾,卻天差地別。沒有人有辦法將各國的變體全都一手掌握。身為舞者,就必須作出抉擇,而且,事情還沒這麼簡單。每一派別又各有其離經叛道的異端:總會有舞者覺得另有更好的方法來組織肢體動作,而帶著一幫人離開,自立門戶。所學者何,也就是追隨哪一位宗師或哪一門派,決定你是怎樣的舞者,決定你想當怎樣的舞者。整理各方的爭論,抽析其中狡辯和夾纏不清的詮釋(暨個人之)兩難,每每教我愈罷不能,但也極為費力。所以,我還要再等一陣子,才開始懂得要問:這些國家流派的差別是怎麼出現的?又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有其歷史淵源嗎?若有,又是怎樣的呢?
那些年,我從沒想過芭蕾未必是當代的藝術,未必是「此時此刻」的藝術。芭蕾的歷史再古老,演出時,不交給年輕的舞者去跳也不行,因此,免不了會染上年輕舞者特屬年代的色彩。此外,芭蕾不像戲劇或是音樂,芭蕾沒有文本,沒有統一的記譜法,沒有腳本,沒有樂譜,僅有的文獻紀錄也極其零散。芭蕾不以傳統、歷史為限。巴蘭欽就鼓吹這樣的看法。巴蘭欽生前於無數訪問即一再解釋,芭蕾來了又去,像花開花謝或濤生雲滅,舞蹈是存在於當下的「瞬時藝術」(ephemeral art);也就是之說,舞蹈純粹「活在當下」──我們說不定明天就不在人世了呢。巴蘭欽言下之意,似乎是發霉的老舞碼,例如《天鵝湖》,就不要再翻出來演了,而是要「日新又新」。不過,這樣的訓誨用在舞者身上卻顯得矛盾:舞者隨目所見不盡皆是歷史?何新之有?在老師身上、在舞者身上,連巴蘭欽自己編的芭蕾,也可見斑斑盡是歷史,寫的全是對往昔的回憶和浪漫的遺風。只是,我們舞者卻以「永不回頭」為信仰的圭臬在膜拜,堅決將目光鎖定在眼前的當下。
之所以如此,便在於芭蕾沒有固定的文本可依循,便在於芭蕾是以口述和肢體動作傳世,像荷馬的史詩,是口耳相傳的敘事藝術,植根於往昔者,只會多,不會少。舞蹈其實也不是一無所本,只是未曾形諸文字:舞者習舞,不一直就是練習再練習,把舞步、變化、儀式、作法練得滾瓜爛熟嗎?這些,確實有可能隨時間而改變或是替換;只是,舞蹈的學習、演出、傳世,作法一直極為守舊。舞蹈前輩向後生晚輩示範舞步或是變化,依舞蹈這一行的倫理要求,後學只能嚴格遵守、敬謹奉行。兩方自然也都認為,老、少兩代傳承的知識經過千錘百煉,當然出類拔萃。以我自己為例,丹尼洛娃教我們《睡美人》的變化組合時,我就絕想不到要質疑她傳授的舞步和風格。她的每個動作,我們一概緊跟不捨。大師教的一切,確實因為有其美感和邏輯,才會備受後輩尊崇。但也因為大師所教的一切是後輩和過去歷史唯一的聯繫,因而不得不奉為圭臬──丹尼洛娃當然清楚這一點。這樣的關係,便是前輩大師和後生晚輩牢不可破的紐帶,銜接起數百年的流變,為芭蕾在過往歷史找到牢固的根基。
所以,芭蕾其實是存在記憶而非歷史的藝術。也難怪舞者一個個像著魔一樣,什麼都要去背:舞步、手勢、組合、變化、一整支芭蕾舞碼。絕非誇大。記憶確實是芭蕾藝術傳遞的中樞。舞者的訓練,便像芭蕾伶娜娜塔麗雅.瑪卡洛娃(Natalia Makarova, 1940-)說的,就是要把舞碼「吃下肚去」,也就是要將之消化吸收,然後長在自己身上。這樣的記憶叫作「身體記憶」(physical memory),亦即舞者會跳的舞碼,是牢牢記在身上的肌肉、骨骼裡的。舞者的回憶訴諸官能,就像法國作家普魯斯特對瑪德蓮蛋糕的回憶,不僅勾起學過的舞步,也勾起手勢和動作,也就是丹尼洛娃說的:舞蹈的「幽香」(perfume)──還有舞蹈的前輩。也因此,舞碼的資料庫不在書頁,不在圖書館,而是在舞者身上。芭蕾舞團大多還會特別指派幾人擔任「記憶庫」(memorizer)──有的舞者擁有非凡的舞碼記憶力,凌駕同儕──負責背下舞團推出的舞碼。這類舞者就像芭蕾的書記(兼學究),將全套舞碼記在四肢、身軀,(往往)還和音樂配合同步,音樂一響,就會觸動肌肉,將舞碼從記憶庫裡抓出來。不過,舞者的記憶力再好,生命也有終了的一天。所以,每消逝一世代的舞者,芭蕾就失去一段歷史。
也因此,芭蕾舞碼的資料庫人盡皆知:少得可憐。「古典舞碼」少之又少,「經典文獻」寥寥無幾。目前我們擁有的古代芭蕾舞碼屈指可數,大多出自十九世紀的法國或是帝俄末年。其他的時代就比較近了: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作品。於後文可知,十七世紀的宮廷舞蹈是留下了些許記載,但是,這類舞譜使用的符號,十八世紀便已失傳,爾後也一直未見換新。以至這類宮廷舞蹈像是切出來的快照,前、後都找不到。其餘,也只剩斑駁的星星點點,滿是漏洞。有人可能以為法國芭蕾應該還保存得不錯:因為,古典芭蕾的基本規則於十七世紀的法國已經編有定制,之後,芭蕾藝術於法國的傳統也始終流傳不輟,迄至今日。不過,真說有,也跟沒有差不了多少。例如《仙女》(La Sylphide)一劇,一八三二年於巴黎首演,但是,首演的版本很快就湮滅無存。我們現在的版本是一八三六年於丹麥推出的新舞碼。《吉賽兒》(Giselle)也一樣,一八四一年於巴黎首演,但是,我們現在看的版本是一八八四年的俄羅斯新編版本。再如一八七○年問世的《柯佩莉亞》(Coppélia),十九世紀的法國芭蕾至今演出依然(多少)沿襲原始舊製的,其實僅此唯一,就這一齣而已。
就是因為這樣,大多數人才會以為芭蕾是俄羅斯人的舞蹈。馬呂斯.佩提帕(Marius Petipa, 1818-1910)這一位法國芭蕾宗師,一八四七年起就在帝俄宮廷任職,直到一九一○年辭世。他在聖彼得堡推出一支又一支新創的芭蕾舞碼。一八七七年有《神廟舞姬》(La Bayadère);一八九○年是《睡美人》;《胡桃鉗》和《天鵝湖》則分別於一八九二年和一八九五年首演,後二者同都和列夫.伊凡諾夫(Lev Ivanov, 1834-1901)合作。米海伊爾.福金(Mikhail Fokine, 1880-1942)的舞作,《仙女們》(Les Sylphides),也是現在依然常見演出的舞碼,首演就是在一九○七年的聖彼得堡。馬林斯基芭蕾舞團調教出來的法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 1890-1950),一九一二年於巴黎推出他的創作:《牧神的午后》(L’après-miodi d’un faune)。再如巴蘭欽,也是出生於聖彼得堡,雖然名下諸多偉大的芭蕾作品都是在巴黎或紐約創作出來的,但是,追究起巴蘭欽舞蹈的根源和訓練,還是要回溯到俄國。以至我們說的芭蕾經典文獻,描寫的傳統一面倒向俄國,而且,論起源,再早也只追得到十九世紀末年。因此,以西方音樂來作比擬,這樣的情況就很像是西方的音樂經典從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1840-1893)才算開始,一待寫到史特拉汶斯基(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 1882-1971),就戛然而止。
不過,芭蕾的相關文獻即使不多,芭蕾於西方文化史的位置卻不容置疑。芭蕾確實是古典藝術。沒錯,古希臘人是不知道有芭蕾這樣的舞蹈。但是,芭蕾一如諸多西方文化、藝術,其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也都和西歐重新挖掘古代希臘、羅馬文物有直接的關聯。在那以後,歐洲各地的舞者和芭蕾名家便將芭蕾看作是復興古典的藝術,致力要將芭蕾的審美理想──暨名望──重新植根於五世紀的雅典。阿波羅(Apollo)於此,便占有一席特殊之地。阿波羅是主掌文明、醫療、預言、音樂的神祇。不同於牧神潘(Pan)和酒神戴奧尼修斯(Dionysus)手中喧鬧的排笛和鈴鼓,阿波羅演奏的樂器是古希臘小豎琴「里拉」(lyre),以溫婉、清幽的樂音撫慰人心。阿波羅高貴的儀表、完美的比例,代表人類的一大理想:節制沉穩、盡善盡美,體現了「人是萬物的尺度」。不止,阿波羅出身高貴,是眾神之神的天神宙斯之子,統帥眾家繆思(Muse)女神的主神。此輩繆思女神,也非等閒,一個個都是文化涵養深厚的美女,同為宙斯所出。還有,她們同為記憶女神倪瑪莎妮(Mnemosyne)之女也非偶然。繆思女神分別主掌詩歌、美術、音樂、滑稽啞劇(mime)、舞蹈(女神泰琵西克蕊﹝Terpsichore﹞)。
不止,阿波羅之於舞者,不僅是理想的典型。阿波羅之於舞者,是具體、有形的實在。舞者每天苦練,不論明知還是無意,為的都是要將自己改造成阿波羅的模樣。不只經由模倣,也不單靠先天條件傲人,另還要發自內心,由衷形之於外。每一位舞者於內在的心眼,都深深烙著阿波羅的英姿,常懷一心追求的優雅、勻稱和雍容,念念不忘。優秀的舞者全都明瞭,單單展現繪畫、雕像裡的阿波羅英姿或是模樣,還不算數。肢體的位置若要煥發萬鈞劇力,舞者就要想辦法變得開化,有文化涵養。所以,肢體的問題,從來就不僅止於賣力鍛鍊而已,還包含品行的陶冶。也就是因此,舞者每天早上在把杆旁邊站好,將雙腳擺出第一位置(first position),神情才會那麼專注。
從法國的凡爾賽宮到俄國的聖彼得堡,迄至二十世紀,阿波羅的英姿始終雄踞芭蕾世界,睥睨一切。阿波羅代表的理想,深植於芭蕾的核心。各地芭蕾名家創作的主題、所思所想,慣常皆以阿波羅為中心,絕非偶然。阿波羅的形象確實是芭蕾歷史的骨架。文藝復興時代的王公、法國的國王,就喜歡把自己扮成阿波羅,身邊還要安排成群繆思簇擁隨行。一支又一支芭蕾舞碼,常見阿波羅身披羽飾、一身金碧輝煌,完美的體態和非凡的比例,在在是芭蕾大師的昂揚身姿和傲人成就的反映。所以,芭蕾這一門藝術從問世之初,就深植阿波羅的英姿。待走到了另一頭,時隔約四百年,巴蘭欽於兩次大戰期間,也在巴黎創作出《繆思主神阿波羅》(Apollon Musagète),日後這一支舞碼他還一改再改,直到辭世方休。於今,舞者依然在跳《繆思主神阿波羅》,阿波羅也依然在將芭蕾往回推到古代的古典淵源。
至於天使呢?芭蕾一樣從一開始就將兩大世界:「古典世界」和「異教徒–基督徒世界」,兼容並蓄於一體。無以計數的輕盈、縹緲、大大小小的精靈、仙子,有的長有翅膀、有的淘氣搗蛋,優游於大自然的空中、林間。這些精靈、仙子,無一不像芭蕾,空靈,飄忽,瞬息即逝,宛如西方世界想像的夢中國度。於此,重點在翅膀。蘇格拉底說過,「翅膀的功用,在於將重物往上抬到空中,而空中便是眾神的所在。所以,凡屬軀體所有的一切,就以翅膀和神的關係最近」。因此,會飛的精靈、仙子當中,就屬天使與眾不同:天使和上帝的關係最近。夾在凡、神之間傳遞訊息的天使,便是連接凡、神、天、地的紐帶。這樣的天使,當然是芭蕾的一切,始終縈繞芭蕾舞台不去,始終是芭蕾的參照點,橫跨不同時代、不同風格,始終是芭蕾藝術追求的境界。阿波羅若是完美的肢體和人類文明、藝術的代表,那麼,天使便是舞者渴望飛翔,尤其是渴望昇華的代表──渴望凌駕凡塵俗世,超脫飛向上帝。
只是,古典芭蕾傳達的難道僅僅是心靈和昇華?古典芭蕾不也是凡塵的藝術,有性、有欲,而且,這一面比心靈、昇華還更明顯,昭然在目?天使於此,一樣是我們最好的嚮導:天使本身沒有性,沒有欲,卻可以(也往往)撩撥起情欲和渴望。芭蕾舞者很少會從他們的藝術感受得到情欲:縱使肢體交纏或是熱切擁抱,芭蕾卻因為脫離現實、扭捏造作、純屬人工製造,但又太費力氣、需要全神貫注,以至舞者涉身其中,很難真的撩起情欲。總之,芭蕾是純淨的藝術:每一動作都要琢磨到精簡之至,純粹之至,不沾一絲冗贅或雜質。芭蕾,就叫作「優雅」。但若芭蕾先天就摒除了情欲,芭蕾往往還是透著濃烈的感性和情色:舞者向來需要公然裸露大片肢體。只不過,這中間若真有絲毫「靈、肉」和「神、俗」兩端拉扯的張力,也很容易化解。芭蕾的舞蹈再放浪形骸,也還是美化過的藝術。
想當初,我決定為芭蕾寫一部舞蹈史,原本是要為我於舞蹈生涯遇上的諸多疑問尋求解答,但卻發現,我的疑問沒辦法單從舞蹈的觀點就求得答案。因為,芭蕾舞劇本身迷離又縹緲,因為,芭蕾沒有歷史的延遞,所以,芭蕾的歷史沒有辦法限定在芭蕾本身來作敘述,而要放進更廣闊的脈絡。只是,什麼脈絡呢?音樂?文學?美術?這些原本就是芭蕾內含的元素,只是於不同時代的分量未必相等罷了。所以,從任一角度切入去談芭蕾的歷史,都有其道理。也因此,我做的便是力求不以僵化的解釋模型為限。例如唯物論,也就是以經濟、政治、社會關係作為藝術主要(或是獨有)的塑造力。或是相反的唯心論,以藝術作品的意義純粹存在於其文本,因而舞蹈應該以其舞步和形式規則來作了解,毋須訴諸舞者的生平或是舞蹈的歷史。二者,我皆不取。
另外,有人主張舞蹈尚未呈現觀眾眼前之前,不算真的存在,這一點我也未能苟同。因為,這樣的看法等於是以藝術作品所引發的觀者回應,而非作品本身之創作,來決定作品的意義。若是循此看法,那麼,全天下的藝術一概難有定論,一概變動不居。因為,這樣一來,作品的價值端看觀者是怎樣的人,而和舞蹈家原本(有意或無意)的意圖無關,和舞蹈家得以運用的語彙和理念無關。走到「觀者獨裁」這一步,依我的看法,徒然益增僵化、時代錯亂的困擾罷了。這樣的情形,和我們這時代執迷於變動和相對的觀點,脫不了關係。只是,即使我們不願率爾反對,勉與同意所有觀點都有其道理,但到頭來,卻只會放任思辨淪為虛妄而已──也就是不管作怎樣的批判和評價,一概變成「純屬個人意見」。所以,我在書裡是在講芭蕾的歷史,但也會拉開一點距離,對舞蹈作客觀的評價。這可不怎麼容易,因為,失傳的芭蕾舞碼太多,總不能拿這樣的舞步、那樣的舞步或舞句(phrase)來作論證就算了。不過,終歸要奮力一試。所以,我的原則便是常懷信心,以開放的心態,一秉所得的證據,建立批判的觀點,試行評論這一支芭蕾舞碼比那一支出色、又何以比較出色等等。若不如此,我們的歷史只會淪為一堆名字、日期和演出的集合體而已,根本稱不上歷史。
不過,我興趣最濃的,終究是芭蕾的形式,這也是當初吸引我一頭栽進芭蕾世界的主因。為什麼這樣的舞步要那樣跳?是哪些人發明芭蕾這般做作又泥古的藝術?於其背後推動的生命泉源又是什麼?法國人這樣子跳,俄國人那樣子跳,又是麼回事?芭蕾這一門藝術又是怎樣體現理想、民族或是時代的?芭蕾是怎麼演變成今天這模樣的呢?
這些問題,我認為可以循兩條途徑來處理。第一條途徑,狹窄而且集中:就是死守身體的動作,投身舞蹈藝術,盡力從舞者的觀點去看這一門藝術。縱使原始資料少得可憐,舞碼又大半皆已亡迭,但也應該未能嚇阻我們吧?於今,以古代和中古為主題的歷史著作,那麼豐富、那麼精采,所根據的原始資料不是還要更少?所勾畫的時代不是還更古老?即使是最稀疏的斷簡殘編,像是有人把芭蕾課上過的一段動作以草書信筆寫下,或是潦草塗寫的舞步組合,都是一盞盞明燈,照亮芭蕾的形式、理念和信念,讓歷史重新活了過來。因此,本書每寫到一階段,我就會重回舞蹈教室,重溫所知的舞蹈──自己跳,也看別人跳,力求對舞者認為他們在做什麼、又為什麼要這樣子做,有所分析和理解。芭蕾的技法和形式發展,是芭蕾歷史的核心。
芭蕾或許沒有連續不斷的歷史記載,卻未必等於芭蕾沒有歷史。還相反:世人跳芭蕾、表演芭蕾,至少有四百年的歷史了。古典芭蕾起自歐洲宮廷,於其濫觴,除了是藝術,也是貴族的禮儀兼政治活動。其實,芭蕾的歷史和國王、宮廷、國家命運的牽連,可能遠大於其他表演藝術。歐洲貴族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的世道流變,芭蕾一體概括承受,而且,糾葛還十分複雜。芭蕾的舞步從來就不僅是舞步;芭蕾的舞步也是一套信念,芭蕾的舞步於一靜一動當中,流露當時貴族階級為自我勾勒的形象。芭蕾和外界的廣大關聯,在我看,便是了解芭蕾藝術的根源:若欲了解芭蕾的源起、了解芭蕾的流變,最好的門道,就是從過去三百年的政治和思想的動盪劇變來作觀照。芭蕾,是由歐洲的文藝復興和法國的古典主義,由各國的革命和浪漫主義,由表現派(Expressionism)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sm),由現代主義(modernism)和冷戰,塑造而成的。芭蕾的歷史,確實是更宏大、更壯闊的歷史之流。
芭蕾的歷史進程,當然也有走到日薄西山的一天。於今,世人普遍視芭蕾為老派、過時的舞蹈;在當今步調愈來愈快、紛擾混亂的世界,芭蕾確實顯得格格不入,扭捏侷促。前一偉大世代走到強弩之末,既恭逢其盛,也親眼目睹其日益衰頹,這樣的變局,在我們不可不謂巨大。我第一次見到杜布蘿芙絲卡,是約三十五年前的事。芭蕾那時還有天時、人和,生氣勃勃一如以往,現在卻大不如前了。不過還有零星幾處地方,有人始終熱愛芭蕾未減,也有幾處地方始終看重芭蕾不輟,所以,芭蕾說不定終有一天能夠重新站回文化旗手的位置。但是,過去三十年,世界各地的芭蕾無一不從高峰墜落卻也是不爭的事實。這樣的事實容或遺憾,也不是有害無益:至少芭蕾不再身陷藝術創作的颱風眼。或許有所失落吧,但起碼目前的失落,也因此給了我們時間回顧過往,思索過往。這樣,我們反而能把芭蕾的歷史看得更透徹,而有辦法真的開始講述芭蕾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