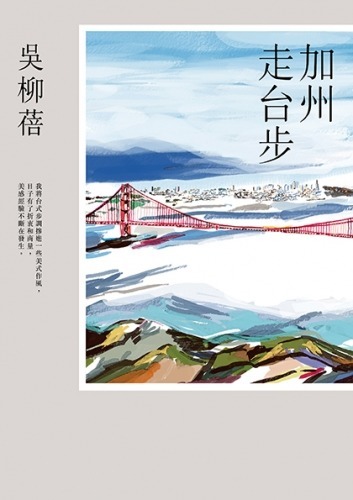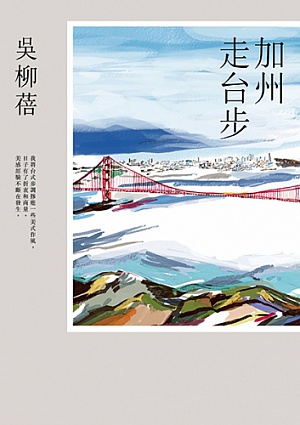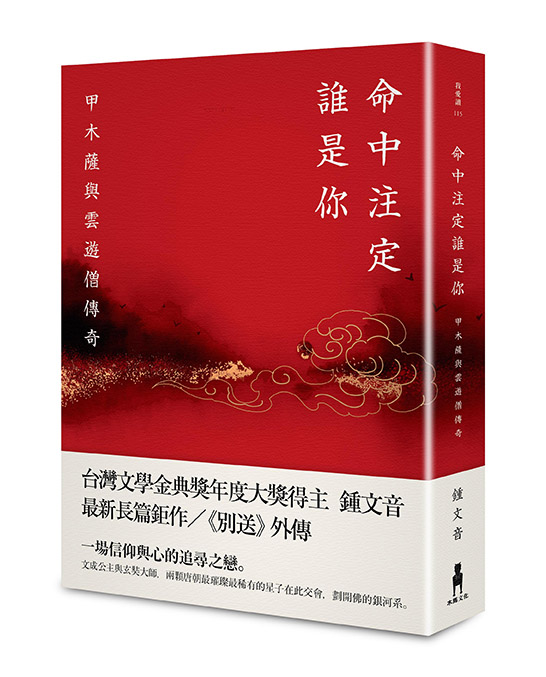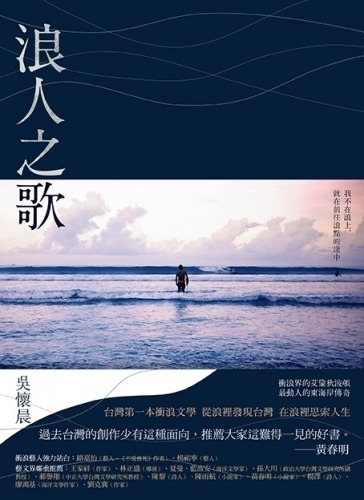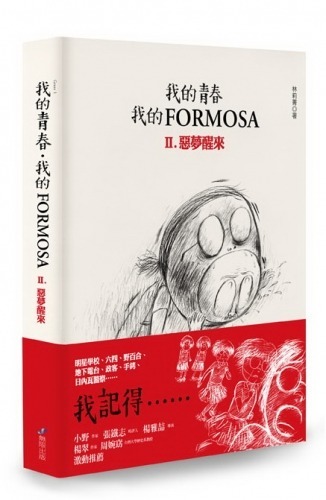我將台式步調摻進一些美式作風,日子有了折衷和商量,美感經驗不斷在發生。
——吳柳蓓
宇文正聯合報副刊主任、羊憶玫中華日報副刊主編、李欣倫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簡媜作家 一致推薦
移居加州的吳柳蓓,帶著故鄉的印記,寫加州瑣細日常。當地的氣候、食物、居所、朋友、娛樂等生活的改變,適應與不適應,書中提到的看牙醫、吃早餐、剪頭髮、練瑜珈、考駕照、曬衣服,皆從小事著眼,寫來如輕鬆詼諧的小品,偶有以物抒情,中華日報副刊主編羊憶玫讚美,「隨性落筆,卻見真章。」作家李欣倫也說,所有物事在吳柳蓓眼中,皆清晰烙下了「Made in Taiwan」 的樸實可愛印記。
本書內容分為:輯一「北加之夏」,以輕鬆詼諧的私人筆調描寫台灣、美國的生活體驗,以此窺探兩地文化異同;輯二「溫哥華的手心」,深入描寫職場與弱勢底層的觀察,兼有旅遊文章、個人情感抒發。身在異鄉,語言、文化的衝擊打破慣性的想法,讓人有了更開闊的人生視野,對於家的意義、親情、愛情有了不同以往的體悟。
本書特色
1.輯一文章皆曾發表於《中華日報》副刊「台美生活日記簿」專欄,輯二的〈小姐,給我一塊錢買咖啡〉〈溫哥華的手心〉〈休假中,請勿打擾〉〈一顆十元,看看喔〉〈水色旅店〉等文章曾發表於《聯合報》副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講義雜誌》、《九彎十八拐》雙月刊,〈一顆十元,看看喔〉收入《2014飲食文選》。
2.一本看似輕鬆詼諧卻真摯動人的散文集。
吳柳蓓(Pepe Wu)
1978年生,彰化北斗鎮人,目前旅居北加州,寫文者。喜歡Plurk、旅行、思考、養花、美食、走路、垃圾話。
曾獲台北文學獎首獎等若干獎項,著有《裁情女子爵士樂》、《移動的裙襬》、《沒有門牌號碼的國度》、《租借日記》。
email:sfcbaby2863@gmail.com
溫哥華的手心
清早六點半,姨丈與阿姨開車送我們到西雅圖火車站,下車後,K繞到車子後面提行李,我們一起跟阿姨、姨丈揮手說再見。
推開沉重大門,旅人四面八方湧向check in櫃台,一天兩班進溫哥華的火車,不是清早就是晚上,大家都選擇早起。K示意我一旁坐著看顧行李,他要排隊拿車票,我依照指示坐在長椅上,行李緊緊挨在膝蓋邊,恍神後時間不知不覺來到六點五十分。六點五十分的旅人面孔仍有一點惺忪,有一搭沒一搭交談著,動作緩慢帶一點猶疑,像剛從被窩伸出的四肢,顫巍巍的對溫度探試。
不遠處有一個盤腿坐在地上的刺青男凝視一本旅遊手冊出神,鬍碴往臉頰方向蔓延,不動時就像一尊塵封悠久的雕像,只為眼前的世界屏息。刺青男的左邊則是一名倚著圓柱吃三明治的女背包客,身上一件削肩背心加上一件超短熱褲跟西雅圖的冷冽初晨有一股不搭調的詭異感,不經意往她胸口一瞥,只見乳溝微微,沁著薄汗,沉重的大背包使得她的身子看起來像一具脊椎側彎的衣架模特兒。跟我一樣看顧行李的人不少,上年紀的老嫗等著等著就打盹了,七點零五分的車站大廳,氣流懶洋洋,人聲沒有鼎沸,連鐘也嫌早。
這是K第三次到加拿大,這一次特別帶上我,他說無論如何要我親自走一遍楓葉國,體會一樣屬於北美領域卻擁有英式風情的國境。平日對於需要面對面的人際往來並不太熱衷,反倒對旅行中的陌生人能輕易的展現親暱與友善,我想除了對旅行的喜愛外,應該是彼此都能明白,旅行中所遇見的人事物都只能算是過眼雲煙,不像與自己有著親疏交集的朋友需要裡裡外外費神。突然想起K說過一句話,旅行中最不可思議的是從陌生人的眼裡找到一樣的目的、一樣的喜好、一樣的感動,而且在同一個moment產生相同的心靈默契。這句話講到我心坎裡去了,完全不需要修飾,sometime,我會訝異一個理工背景的男人說出這種感性的話,然而我更相信他移轉自身古典音樂素養到日常生活細節的能力,甚至在我之上。跟一個人長時間相處,需要具備「天外飛來一筆」的思想魅力,以取悅日趨平淡的兩人生活。
對我們來說,去一趟溫哥華可以順道拜訪住在西雅圖的長輩和親戚,或許停留一夜、兩夜,不管是夜裡窩在客廳沙發看電視,或是白天到碼頭買一杯西雅圖咖啡,逛逛熱門的魚市場,都會讓我像孩子一樣雀躍萬分。人在海外,親情存款比美金存款來得真切有厚度,不只是我,周遭的朋友常常盼一個親人來訪,像盼個孩子一樣困難,雖然表面上滿足了人生視野的追求,內心的親情平台卻也因為移居的選擇不由自主的塌陷了。每當我為這種事鬱鬱寡歡,K總是在一旁安慰我,他說現代人忙碌,感情難免疏離,住在屏東的哥哥也許十年八年才見一次遠嫁台北的妹妹,步調差了十萬八千里,何況人在海外。我不會承認我若是那遠嫁的妹妹,會如此殘忍不見哥哥這麼多年。儘管不願如此,但是現實的情況真能讓我隨心所欲嗎?這正是身為人最艱難之處,人總是習慣性的駝著情感包袱,卻又忍不住哭訴這樣的方式很累。長我三歲的哥哥一向斯文,可是當手足被欺負,他永遠第一個跳出來揮拳,也許揮拳時心裡是很害怕的,但是他知道比他脆弱的弟妹除了倚靠他還能靠誰?爸媽要忙的事很多,大人習慣用遺忘來擺平傷痛,比如他們早就忘記很久以前被某個童伴推倒流血不止卻沒有大人出面關心的哀傷童年。我相信每對父母在百年之後,寄望一生經營的親情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就算日後遠颺,手足之間的情分還得保持溫暖,直到天荒地老。
終於拿到票了,K將火車票收進皮夾內,看我哈欠頻頻眼眶滿是水氣,瞄了角落的café,問我要不要喝咖啡。也許是太早的關係,café裡除了櫃台站了一名女服務生外,seat area空無一人,紅色的open燈寂寂寥寥的亮著,好像映照著那些來來往往,形形色色,彷彿沒有終點的旅人足跡在孤獨裡自醉。和K坐在小圓桌飲著咖啡,胖胖的女服務生端來起士蛋糕,望了精緻的蛋糕一眼,食慾還沒醒,K倒是一口接一口。女服務生端來蛋糕時順口說了enjoy,我抬頭看她,正好看見稜角分明的亮橘色嘴唇一張一闔的,晶瑩剔透得像一尾浮在水面的金魚好性感。突然有一種錯覺,眼前的女服務生是西雅圖的熾熱夏天。
登車的時間到了,K拖著行李走在前方,我端著未完的咖啡跟在後頭。沿著列車尋找我們的車廂,一名高大的站務人員湊近看了K手上的車票,指著不遠處的第五車廂說over there。這列終年往來西雅圖、溫哥華的車廂設計有點高,幸好有一張高低凳置在廂口的前方,方便旅客攀爬。K放好隨身行李,將iPad插上耳機,雙手交握在肚腹,閉上眼睛準備補眠,意思是,take your time,他不管我了。火車鏗鏗鏘鏘往前移動了,車內的旅客有夫妻檔、年輕情侶、姊妹淘、兄弟檔、背包客以及family,交談的聲音很輕,所以車廂內的旅客都能清楚聽見坐在中央靠窗的一名金髮男孩提高嗓音問了身旁的媽媽可不可以吃洋芋片。列車沿著海岸線行駛,經過一座又一座質樸小鎮,在鎮與鎮之間的景色不含糊,一邊是一望無際的草原,另一邊則是沒有盡頭的海平面。草原那側,柵欄裡圈著幾匹駿馬以及閒散的牛群,火車以中等速度經歷了牠們生命中的某一個時刻。至於海平面,太過一望無際的遼闊,盯太久好像會把心給丟了。
火車停駐的站大部分都很迷你,載客量也不算多,月台冷冷清清帶點殘破的味道,像流浪者的臨時居所,有一股二十世紀loft工業的頹廢質感。對一般人來說,從西雅圖到溫哥華,自行開車只需兩個多小時,只是搭火車可以節省精神,但不是最方便的選擇,迷你小站正因為少了人群的洗禮,才顯得更加蒼老和守舊吧。K睡沉了,呼吸聲穩穩的,我了無睡意,盯著前方的即時螢幕讀著奔跑中的火車捨不得把眼睛閉上,看著它一寸一寸的移動,就好像搭機時盯著飛行羅盤,它是很明明白白、分毫不差的指引著遠方的目的地,讓你知道人生的最終目的在哪裡,不是得過且過的那種。
漸漸的,周圍的交談聲有些重,陸陸續續有旅客離開座位去美食包廂覓食,K醒來問我餓不餓,我嗯了一聲,他便拿掉耳機走到另一座車廂買食物。K買回兩個三明治,兩人邊吃邊聊,有一搭沒一搭的,金黃色的雲層沉甸甸的幾乎要drop down到海平面,遠遠看就像老天爺隨筆完成的水彩畫,掛在天邊給有緣人驚艷,同時曇花一現。最終還是將漫長的海岸線走完了,當列車停靠在溫哥華火車站,迎接整列火車的是一座灰色的冷城市,玻璃窗沾著數不清歪歪斜斜的雨絲,陽光瑟縮在很深的雲裡,穿不透的寒意沖淡了我內心的興奮之情。K從隨身行李取出兩人的厚外套,他說,穿上吧,等一下排隊過海關會擔誤一點時間。我把外套穿上,下車時看見兩三名壯碩的站務員將旅客行李搬下車,除了行李箱,還有自行車,裝吉他的大盒子和一些看不出裝什麼東西的普通紙箱。
三十分鐘後,我們順利走過海關,K一手拖著行李,一手牽著我離開火車站,雨還稀稀疏疏的落著。這雨不算雨,停停頓頓,柔柔魅魅,像大瀑布激起的濛濛霧氣,才過一個馬路口,頭髮就像覆蓋一層薄薄的水珠,遠遠看像蝨子。
到火車站對面候車亭等公車,約莫十來分鐘公車便來了,年輕駕駛一一問候了上車的乘客。我內心有點意外,可能習慣北加州公車司機獨善其身的瀟灑脾氣,首度交手的溫哥華司機的友善姿態讓我對這場要下不下的毛毛雨開始不那麼惱火了。第一次在溫哥華搭公車竟然像在台北搭公車般輕鬆自在,沒有想像中的緊張和疏離,讓我幾乎要在車上打毛線或寫一篇日記。我不願深入去想這份安逸感是因為車上華人面孔較多的原因,那顯得太拙劣、太狹隘,也太可惡了,不過我又不能全盤否認內心深處的人種恐懼,是我自己的trouble,我活該要過得如此缺乏安全感。想起頭一次在美國搭公車,僅一、二十分鐘的車程,K從辦公室打了三通手機給我,不斷提醒我注意這個注意那個,最大原因是他在美國待了三十多年,從沒搭過公車,對公車底細一無所知,加上不時傳出槍擊或挾持事件,讓他對公車全無好感。他對公車的概念直接影響我,讓我莫名其妙患上「搭公車恐慌症」,幸好只會在美國發作,一回台就自動痊癒。
K一邊看地圖一邊喃喃自語,還要分心觀察車外的景色,沒多久急急忙忙按下車鈴,我也慌慌張張跟著下車。一下車才發現下錯站,預訂的旅館在史坦利公園(Stanly Park)附近,若在此站下車,用走的可能要走上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K有點懊惱,一轉頭發現公車竟然還停在原地,二話不說奔回公車旁,司機笑咪咪的讓我們重新上車,我倆在眾目睽睽之下彆扭的坐進原來的第一排,後面乘客的表情如何,我們只能裝傻。
下榻的旅館在公園的上方,走路約十分鐘可到達,熱鬧的主街也相隔幾條街而已,我們的房間在二十三樓,那樣高的視野幾乎將整座公園和更遠處的海景一覽無遺。站在陽台仔細端詳眼前的山水,厚重的雲層被風畫開了,陽光像一把開褶的橘色扇子,穿梭在棟與棟之間的縫隙,溜進每一扇將醒未醒的窗子。一股若有似無,略為慵懶的英式質地,像初夏早晨的葡萄園,熾烈又冷潔的籠罩著全溫哥華。
眼前大大小小的建築呈現了時代拼裝的面貌,真要用一段周延的文字拿捏其實不容易,世界上每一座知名的城市有著成千上萬旅人的自我詮釋,讀別人的,未必適合自己。在熟悉溫哥華之前我以為她大概如張翎筆下那種沾染時代灰塵的體質,可是當有一天走進她的肚腹,感覺她像一個二十歲年輕有勁的yoga老師,舉手投足之間盡是迷人。
隔壁陽台忽然傳來兩名男人的說話聲,還有一絲大麻煙的味道,我和K只好中斷觀景的雅致,進房將行李稍微整理後便出門了。走在深長但不寬闊的林蔭道上,K突然轉頭對我說:「這條路像不像台北市的敦化南路?」我大笑,在台北西門町長大的男孩不管走到哪裡都會記得把內心的台北大衣拿出來抖一抖、晾一晾,順便跟別人比畫比畫。其實他不說,我倒覺得比較像仁愛路,捕捉感覺是一瞬間的事,各有各的眼光。我們很安靜的走過那段幽深的林蔭,頂上的太陽越中午越大膽,赤裸裸灑在每一條馬路上,原本穿在身上保暖的毛衫顯得太over,拿在手上又太累贅,困擾之際,K一把取過衣服,他知道這件薄衫最後的下場不是丟在沙灘上無人認領,就是離奇消失在某一家餐廳的椅背上,倒不如自己收著放心。
走出旅館大廳開始,我與K的手始終牽在一起,儘管手心已經黏呼呼了卻沒有甩開的打算。這裡是溫哥華,不同於台北,不同於加州,再熟悉也只是一種自戀的幻覺。K牽著我的手,怕有意外、怕有閃失,我沒有他那份憂慮,牽著他的手,彷彿牽著一輛行動溫哥華,走在大大小小的街道,何時該轉彎、何時該過馬路,我一無所知卻十足的篤定。在無數次出遊之後,K總算徹底了解我空間智能的低劣,行前的功課都是他的,我的責任是「出門」。
史坦利公園最熱門的活動是騎自行車,原本打算租車觀賞公園全景和海灣面貌,不過在公園走了三十分鐘,看到許多家長和小孩騎車亂竄的畫面突然就膩了,加上腿痠,於是放棄租車的想法,直奔海邊覓食。餐廳一間晃過一間,門口的menu讀了又讀,就在尋找最適合味蕾餐廳的間刻,我發現自己竟然無可救藥的愛上海邊這一帶。集熱鬧、便利、美景、悠閒於一身的溫北地帶,在我眼裡幾乎找不到缺點,於是我衝動的對K說:「退休後咱們搬來這裡?」K不可置信的表情說:「妳瘋了,這裡冬天很冷。」我說下雪更好,景色多美多美。K說我愛上的只是表面,冬天白雪皚皚雨勢不斷,很容易染上憂鬱症。「所以溫哥華有很多憂鬱症患者?」我問。K沒回話,但是我知道雨天是他的頭號敵人,更別說雪天。加州乾燥,只有入冬幾周濕冷,一旦進入雨季,柏油路又濕又滑,駕駛人會慌了手腳,我們常在冬雨連綿的highway遇見把車開得坑坑疤疤的駕駛人無從閃躲起。溫哥華的冬天,困住的不只是當地人,還有K的情緒。
接下來幾天,我們走過Gastown,在蒸汽鐘底下拍了兩張端咖啡的傻瓜合照,一連三天開車到列治文吃飲茶,上山看老鷹表演、棕熊睡覺以及原住民的陳年家當。然後傍晚回到downtown,吃過一間又一間各國風味餐廳,也因此誤踩了幾家地雷但也無所謂。旅溫倒數第三天,我們搭船進維多利亞島,隔天早上跟團到布查花園(Butchart Garden)賞花。導遊說我們此行早到了,園方每年六月開始在晚上施放璀璨煙火秀,據說是全世界最貼近地面的一場煙火。數年前K與家人同遊布查花園時看過那場煙火,他一絲不苟的對我口述那場煙火的細節,彷彿我已經親眼目睹了。其實沒親眼見識也無所謂,「全世界最○○」的東西我從來不執著,人生如果有足夠的隨興,就不容易跟生活的邊邊角角扼憾或過不去。
沒記錯的話,北投陽明大學校園裡也有一家叫布查花園的餐廳,有一年跟一名女性朋友參加詩人陳克華的新書發表會就在布查花園餐廳內。當年的餐廳裝潢和餐點滋味有點忘了,但是布查這個名字始終印象深刻,也許是為了多年後的維多利亞之行而提前在我腦中植了記憶。原來,在國外遇見與家鄉雷同的人事物,我也如K一樣,隨時將內心的台北大衣拿出來取暖。
整整九天的時間,我和K攜手把心中的溫哥華摸了一遍,九天不夠釐清巷弄裡的洞天,對人情紋路的掌握也有點粗糙。粗糙有粗糙的層次,美感經驗隨時都在發生,走在早上微冷、中午偏熱的街道上,我的敏銳一如張口的大公獅,厚重且沉溺的感受英美風情的長短之爭,然後有了一種感動,像被溫哥華的大手緊緊牽住,不是我踩著她的輪廓以行,而是她從來沒有離開過我。
從旅館check out後,K一手牽著我,一手拖著行李,搭船離開時的手心依然暖呼呼的,航行三個半鐘頭之後,西雅圖在望,溫哥華漸漸落在眼睛看不見的遠方,只是眼睛,我的心從沒離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