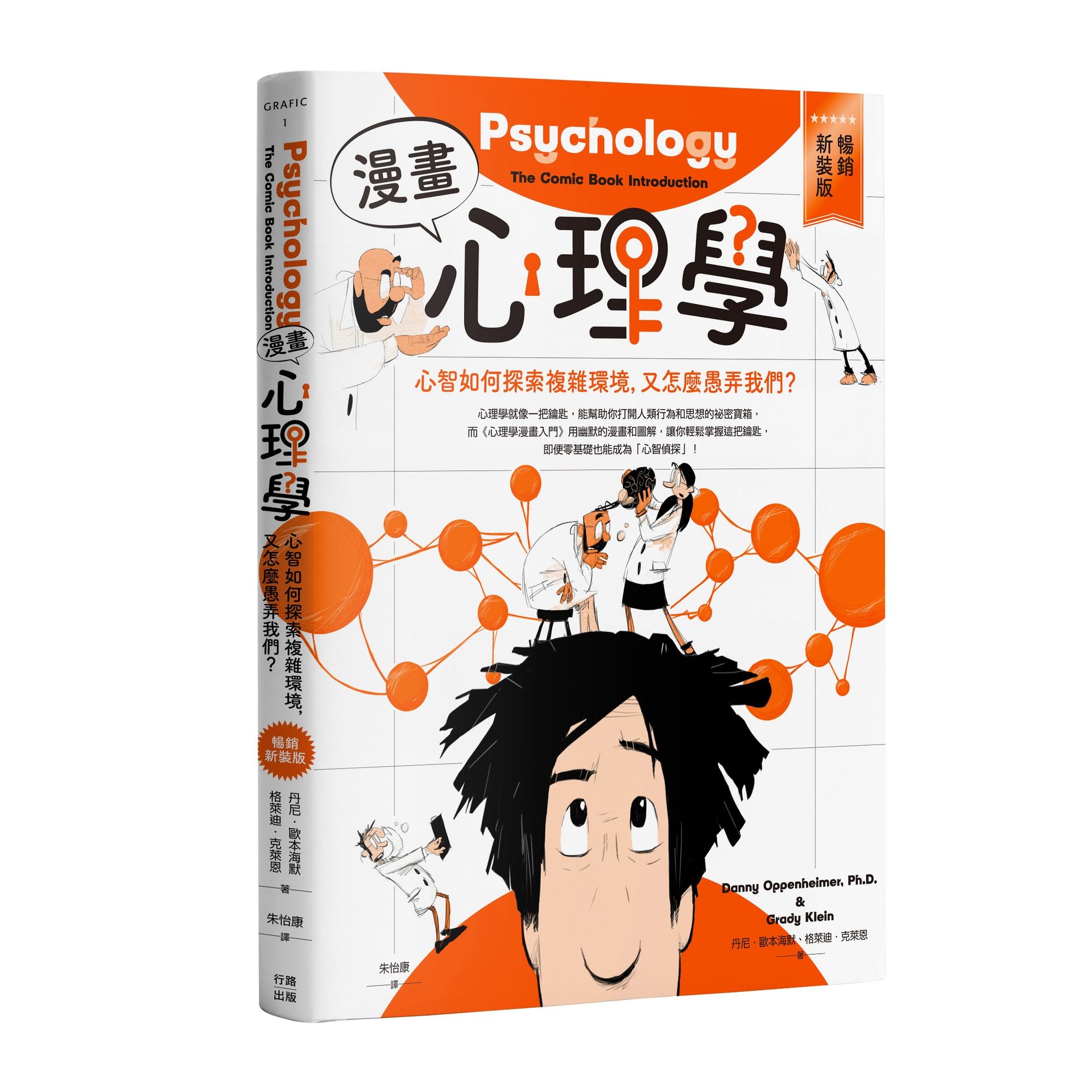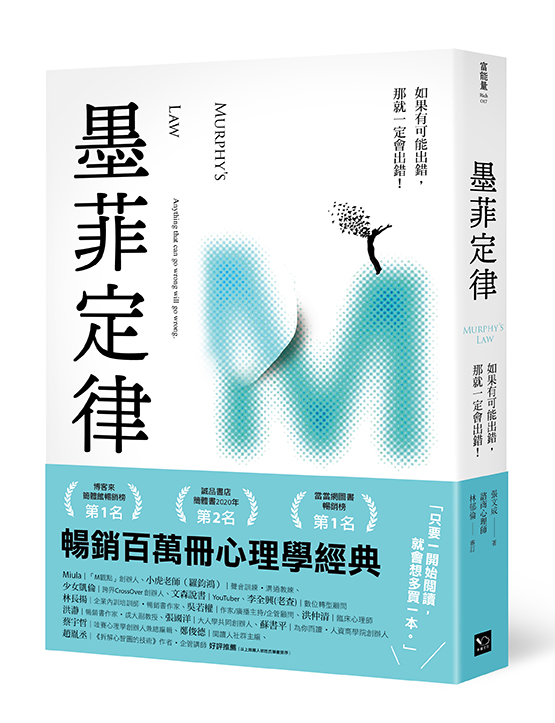人們總是問我「你好嗎?」
他們會強調「好」這個字,所以我知道他們是認真想知道。
但我從來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問題。
我要如何用簡單幾句話總結我目前傷心/寂寞又一團糟的人生呢?
★經典愛情喜劇電影《電子情書》編劇擁抱熟齡人生的真情告白
★《美麗佳人》、《浮華世界》2022年度最佳回憶錄
★《時代》、《出版人週刊》、《Bustle》等各大媒體2022年度最期待書籍
---------------------------------------------------------------------------------
迪麗亞生於紐約市,是個不折不扣的都市女子,也是知名的暢銷書作家、編劇與製作人,家喻戶曉的愛情喜劇電影《電子情書》就是她的代表作。長年書寫愛情的她,人生故事卻比她筆下的電影更加峰迴路轉。
年過七十之後,迪麗亞接連痛失最親近的家人,姊姊死於白血病,結縭三十載的丈夫則因癌症去世。晚年獨居的生活充滿未知與不安,但她努力調適,在《紐約時報》撰寫專欄。意外的是,她因此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來自一位名叫彼得的醫師,兩人的關係也從一開始純粹的精神寄託,逐漸昇華為愛情。然而,她卻在此時被診斷出白血病─那個多年前帶走姊姊的疾病,現在也找上她了……
─
在本書中,迪麗亞描述至親至愛之人的死亡、浸沐於晚年愛情的喜悅,乃至對自身疾病與死亡的恐懼。全書的所有內容,奠基於她在這段期間所有的電子郵件、簡訊、信件草稿,以及通話紀錄。面對由現狀改變而來的各種情緒,她以文字誠實以待,坦然分享她真實不過的煩惱、不願直面的難題、心中的種種猶豫。
#「感受到自己活著,幾乎可說是我最原始的需求。
於是我的內心起了衝突─想要與死亡離得夠遠,知道自己能活得多精采。」
在失去所愛之人後,你要做什麼?沒有人知道問題的答案。如同迪麗亞所焦慮的,「我沒辦法和一個陌生人展開新生活,我沒辦法再次把自己的人生交給某人,重新開始」。這正是因為,對每個活著的人而言,恐懼是生活中的背景雜音。當我們剖析每個人的人生經歷,會發現人人都活在過去經驗的陰影下並受其影響。
人生的變動猝不及防,但迪麗亞並未逃避,而是坦然面對自己的情緒與感受。因此,本書也講述她對生命境遇的感慨,本質上也是一封獻給她自己以及她生命中所有人的情書。
#「我們能擁有這段時光,是何其幸運。
有時候,我甚至難以接受命運竟對我如此溫柔。」
有人說晚年人生有如孤島。迪麗亞極其幸運,每一封來自好友的問候、鼓勵打氣,更為患病期間的她建造了最堅實的後盾,讓她始終被至親好友環繞,度過身心最脆弱、最憂鬱的時刻。
儘管擁有好到不可思議的運氣,迪麗亞仍樂於經營關係並享受所愛之人的陪伴。這不僅是一種天賦,更是祝福。或許迪麗亞的人生遭遇能讓境遇相仿的你因此改觀,以一層又一層的幸運包覆過往的不幸,為熟齡人生的各種收穫而驚嘆不已。
各界好評
「與其說這是一個女人失去丈夫的故事,不如說這是一個女人在七十二歲時再次墜入愛河的故事……許多人的愛情故事或對愛情的渴望,大多並不轟轟烈烈,但伊佛朗的故事激勵了我們……如果有一種回憶錄是讓人讀了之後更感受到生命的美好,那麼本書就是這樣的一本回憶錄。」─《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這本回憶錄趣味橫生、極其美麗,有時甚至令人感覺十分魔幻。作者對老年生活保持開放心態,而她所做許多決定雖然帶有風險,卻也令人嘖嘖稱奇。」─美聯社(The Associated Press)
「儘管本書有許多溫馨的時刻,但伊佛朗在敘述她的痛苦經歷時也毫無保留,這個逆轉勝的故事將震撼所有的讀者。」─《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迪麗亞.伊佛朗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代言人,也是一位文字精巧細膩的作家。如果你正在找一本書,一本告訴你何謂愛情、婚姻、友誼、家庭、創意、失去、救贖,甚至是有關於你的電信公司,那就別再找了,你需要的正是伊佛朗的這本回憶錄。在本書中,伊佛朗翱翔其中,帶領我們一起飛翔─充滿個人風格,這是一本極美的回憶錄。」─艾狄安娜.翠吉亞妮(Adriana Trigiani),《白朗峰上的約定》(The Shoemaker's Wife)作者
「本書將使你再次相信愛情,也相信世上確實存在奇蹟。除此之外,人生一切都非常、非常有趣。」─莎拉.鄧(Sarah Dunn),《現代關係》(The Arrangements)作者
「迪麗亞巧妙且幽默地告訴我們,人生處處有美好的事。本書是一本偉大、美麗的著作,證明在生命最黑暗的時刻,希望與意義永遠都在。不知何故,我總覺得書中潛藏著所有人生大哉問的答案,讓我就像那些正經的存在主義者和探索者,在拿起這本書之後便無法放下,一口氣就讀完了。」─娜塔莎.雷昂(Natasha Lyonne),艾美獎提名演員
「我愛死這本書了。這是一本講述悲傷與疾病的回憶錄,但它在本質上也是一封獻給她生命中所有人的情書,而且是最美的一封。因為迪麗亞總是選擇活得快樂,選擇結交朋友、選擇去愛;她就像一座噴泉,心中滿是感謝,將所有絕望轉變成閃閃發光、灑落彩虹的光芒。」─凱瑟琳.紐曼(Catherine Newman),《幸福是一場災難》(Catastrophic Happiness: Finding Joy in Childhood's Messy Years)作者
「只有鐵石心腸的人才能不被伊佛朗的經歷所動容,本書關於晚年愛情和疾病,既溫柔又充滿魅力。伊佛朗向讀者誠實袒露她治療白血病的過程,以及她在過程中所遭受的恐懼與痛苦。不過,幸好她是個天生樂觀的人,總是能在最黑暗的時刻找到快樂與幽默─因而這本精采的回憶錄,是對恆久的愛情與友誼的一首頌歌。」─喬安娜.拉科夫(Joanna Rakoff),《紐約追夢日記》(My Salinger Year)作者
洪仲清|臨床心理師
高愛倫|作家
彭樹君|作家
黃惠萱|臨床心理師
詹慶齡|資深主播
─感動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列)
迪麗亞.伊佛朗(Delia Ephron)
1944年生於美國紐約,作家和愛情喜劇劇作家。曾為許多知名電影擔任編劇,包括《電子情書》(You’ve Got Mail)、《來電傳情》(Hanging Up)、《牛仔褲的夏天》(The Sisterhood of the Traveling Pants)、《神仙家庭》(Bewitched)等。她和身為著名導演的姊姊諾拉.伊佛朗(Nora Ephron)共筆的音樂劇作品《愛、失去,和我身上穿的》(Love, Loss, and What I Wore)曾在百老匯劇院上演兩年之久,並在全世界公演。
著作橫跨文學至童書等各大文類,著有《紐約時報》暢銷小說《錫拉庫薩》(Siracusa)、《三人行必有我獅》(The Lion Is In)等,散文集有《姊姊、母親、先生與狗》(Sister Mother Husband Dog)等,以及生活風格書《吃得像個孩子》(How To Eat Like A Child)等。
Twitter|@DeliaEphron
傅恩臨
專職譯者。曾在美國求學、工作、育兒。當媽後誤打誤撞一腳踏進了翻譯的世界,進而愛上文字工作。在欣賞孩子一點一滴成長茁壯的同時,也在翻譯過程中一字一句地斟酌出每一件作品。譯有《我的骨頭知曉一切》(二十張出版)。
第一部──離開
Part One: Left
第二部──彼得
Part Two: Peter
第三部──插曲
Part Three: Interlude 2017
第四部──靈藥
Part Four: CPX-351
第五部──烏雲
Part Five: Dark Clouds Part
第六部──蛻變
Part Six: O to A
第七部──歸處
Part Seven: Home
致謝
Acknowledgements
試閱1:〈第一部:離開〉(節錄)
我們最後一次和癌症醫師碰面時,他遞給我們一張「不實施心肺復甦術」(DNR)的同意書,要我們把它貼在冰箱上。「他們通常都會往冰箱門上找。」他說。他口中的「他們」,是指急救人員。
我希望傑瑞可以在家中過世,他也希望如此,但我們並沒有對此多做討論。我對此很執著,因為我認為讓他在自己的床上離世,是我能夠給他的一份禮物。我們的臥房採光良好,牆壁是淡雅的薄荷綠。所以我想,身為作家的他,狀況好的時候可以坐在書桌前寫作;若他需要打個盹──如今他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如此度過──他可以在他的沙發上小憩一會兒。
我們很喜歡住在第十街,這裡是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綠葉成蔭的美麗街區,也因此,我實在沒有辦法讓他在某個顯然是讓人等死的地方走向人生的終點。
我們重寫了遺囑,更新了健康照護的代理人。
我也開始演練獨自一人要如何生活。我會和朋友出去喝咖啡或參加活動,在回家的路上,我會告訴自己,想像你現在回到家,傑瑞已經不在了。他不會在那裡聽你分享、咆哮、大笑,也不會在那裡安慰你。
要預備自己面對未知、面對沒有他的人生,我發現我需要感受到自己還活著。我需要在街道上快步前進,我需要出門、和朋友相處。我不想要死。我不是指我不想和傑瑞在一起,然而感受到自己活著,幾乎可說是我最原始的需求。於是我的內心起了衝突──想要和傑瑞共赴黃泉,同時也想要與死亡離得夠遠,知道自己能活得多精采。
我在三十歲出頭時遇見傑瑞,那時我正以作家的身分逐漸展露頭角。在我們交往的第一年,我的書《吃得像個孩子》(How to Eat Like a Child)出版了,我還記得他在隔壁房間邊讀邊笑的聲音。
傑瑞是一名劇作家和編劇,那時他在紐約參與《舞廳》(Ballroom)的演出──這是一齣根據他的電視電影《星塵舞廳皇后》(Queen of the Stardust Ballroom)所改編的音樂劇。某一天,我們的一位共同朋友邀他到我的公寓,我們一拍即合、墜入情網。我覺得他就是我尋覓大半輩子的伴侶,他也心有同感。他總是把鬍子修剪得整齊清爽,頂著一頭濃密的淺棕色頭髮。他有著深情的褐色眼睛,而他的聲音平滑順耳,是完美的男高音。我們的關係就像所有的關係一樣,有其獨特的爭執點和挑戰,然而多年來,我們之間的歧異卻使我們更加緊密。我們知道我們是天生一對,而我們能找到彼此,更是全天下最幸運的事。
在認識傑瑞之前,我對愛情所知不多。我在比佛利山莊長大,父母都是劇作家,也是彼此的最佳搭擋。你應該會在特納經典電影頻道 (Turner Classic Movies)看到他們所寫的電影:凱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和史賓塞.屈賽(Spencer Tracy)的《電腦風雲》(Desk Set),佛雷.亞斯坦(Fred Astaire)和萊絲麗.卡儂(Leslie Caron)的《長腿叔叔》(Daddy Long Legs),還有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在當中大唱「熱浪來襲」的《娛樂世界》(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我在他們的期望中成長──他們希望我們四姊妹全都成為作家──但我酗酒的母親對我相當冷漠,她在五十幾歲時便因為肝硬化過世了。我父親比較慈愛,但他總是焦慮又黏人,不僅有躁鬱症,也同樣嗜酒。
傑瑞卻完全理解我。這是我始料未及的,因為我從來沒想過會有這種事。他真心愛我,而且培養我的才華。當我試著精進文筆,完成各種不可能的任務時──首先是幽默小品、然後是短文、電影劇本和小說──他一路引導著我。若沒有他,我永遠都無法找到自己的方向。
作家永遠是作家,這份自我認同更勝於任何身分,是一生的呼召。我和傑瑞都知道這點,並以彼此為榮。我瘋狂地愛上他,而且非常享受和他對話的時光。他對人性有極為深刻的理解,總是觀察到我未曾留意的事情,而我也能指出他的盲點。和他討論人類行為和背後的動機,總是帶給我們源源不絕的樂趣。
然而,他就快要不在我身邊,愛我、和我說話、和我天南地北無所不談、甚至說些無聊的廢話了,例如他在想些什麼,外頭發生什麼事,為什麼某件事讓他或讓我不開心、甚至把我們其中一人逼瘋。他再也不會在家裡晃來晃去,心不在焉地吃著巧克力蛋糕。他再也無法和我討論我或他自己在寫作上遭遇的問題,某個角色應該怎麼做,另一個角色會有什麼感受,劇情應該如何發展。傑瑞很懂戲劇,他不僅能編劇,還會教導。他就是我的老師。
他在布朗克斯(Bronx)一個龐大的猶太社區裡長大,他的世界裡充滿了姑姑阿姨、叔伯、堂/表兄弟姊妹,以及庸俗的文化。那是個充滿活力的環境,但同時也極度無知和愚昧。傑瑞從小就很有音樂天賦,他在年幼時就可以將聽到的任何樂曲用鋼琴彈出來。「他已經會彈了,何必上鋼琴課?」他的父母這麼說。他的祖父母在家中自行調製廉價烈酒販售,他的父親則販賣人造珠寶。他們賺來的一丁點錢,都被拿去賭博了。傑瑞的父親還會打破他的撲滿,偷他的硬幣。他們家裡幾乎沒有什麼書。這世界有太多可供創作的題材,傑瑞確實也寫了不少,但他的家中卻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滋養這名作家的夢想。
傑瑞是他們家的異類。我們一起去上踢踏舞課,也熱愛戲劇,在大部分的事情上都意見一致。我們都喜歡出國,而且通常就只是在國外走走晃晃,坐下來喝咖啡。跟他訴說心事總是能得到很大的安慰。
他是我真正的家,也是我第一個避風港。
到了九月的某一天,傑瑞在四處走動時顯得更為吃力,例如將甜甜的喝水碗放在地上這種簡單的小事,都會讓他感到頭昏眼花。甜甜是我們鍾愛的哈瓦那犬。我在和內科醫生談過之後,啟動了安寧照護服務。我們得到社工、護理師和靈性諮商師的協助。我們家唯一的敬拜活動就是寫作,但基於傑瑞即將不久於人世,我就快要失去三十七年來的靈魂伴侶了,或許我們當中會有人需要一些屬靈上的協助。
我對於那段時光的記憶已經模糊了,因為我總是處於焦慮狀態,但我記得在居家安寧照護服務的第一次接案面談中,對方告訴我,如果傑瑞跌倒了──他已經跌倒過一次了──我應要打九一一,但當救護人員抵達時,我可以給他們看不實施心肺復甦術的同意書和健康照護委託書,這讓我有權代替他拒絕醫療處置。我應該請他們把他抬起來、放回床上就好。
我記得我至少接收到兩次這樣的指示,一次是安寧照護的工作人員在電話中告訴我,一次則是出自團隊裡的某位服務人員。
如果我扶著傑瑞,他還是可以走路,所以在安寧照護的護理師第一次來訪後,我們去了附近的Le Pain Quotidien,正當我們吃著酪梨吐司之類的東西時,傑瑞說,「安寧照護,我不確定。我想,進安寧也可以吧。我現在對此沒有什麼感覺。」
「有時候你得花一段時間才會知道自己有什麼感覺。」我說。
那天下午當我回家時,我發現我們貼心的遛狗員蘿倫和傑瑞正在啜泣。
「怎麼了?」我急忙把蘿倫拉到門外問她。
蘿倫說,她問傑瑞狀況如何,結果他才剛說完「我進安寧照護了」就崩潰了,於是她的情緒也跟著潰堤。
我幾乎要笑出來。這就是傑瑞,在遇到蘿倫後才發現自己很沮喪。但這其實不好笑,一點都不好笑。
我就只是站在那裡,也沒有伸出手去抱著他。不知道為什麼,我就只是站在原地。
我在那一刻的失敗──哎,這真的是一種遺棄──一直困擾著我,讓我夜不成眠,我覺得儘管我試著為他做每一件事,卻仍力有未逮。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在那一刻辜負了他,是因為我對他死亡的恐懼和傷心嗎?我在害怕嗎?是因為我對那一刻毫無準備嗎?不過我對當時的任何時刻都毫無準備不是嗎?我為什麼沒有去抱著他?我是冷酷的人嗎?漠不關心會讓我覺得比較安全嗎?
我丈夫的攝護腺癌已經擴散到骨頭了,所以若我環抱著他,可能會傷到他。不過每天晚上,我們總會在十指交扣中入睡。他沒有談太多真正關於死亡的事,或許這是我的錯──因為在這件事之後,我總覺得一切都是我的錯。或許我在逃避吧,我也不知道。有一次我們告訴對方,覺得能與彼此共度一生是多麼幸運,而傑瑞說他並不害怕。
不過我知道,當我出門或在書房寫作時,他是很想念我的。「我需要你在我旁邊。」他說,不過不是用命令的口氣,反倒是訝異我怎麼不在他身邊。
他說他唯一擔心的,是我獨自一人。
(摘自:《老派情書》,〈第一部:離開〉)
試閱2:〈第七部:歸處〉(節錄)
除了身體上的諸多限制,我在心理上也尚未恢復。我與人相處時會感到焦慮、心裡充滿不確定感──而且我也不想與太多人接觸。關於我的病,我應該透露多少?他們會想要聽嗎?他們會不會不知道如何和我互動?我覺得自己與世隔絕,同時也很脆弱。
一想到無所不在的病菌可能會讓我一命嗚呼,讓我緊張又焦慮。
基本上,我得從頭學習每件事情。我毫無肌力,一點都不誇張。我拿著不到二點五公斤的啞鈴,卻覺得他們彷彿有一噸重。
我得學習如何從坐到站。一開始我需要雙手輔助,然後再學習單靠腿的力量站起。更困難的是,我得學習如何在地板上以坐姿站起來。當我坐在地板上試圖起身時,我覺得我乾脆這輩子都躺在地板上算了。然而,當我不斷嘗試再嘗試,然後突然成功時,那種感覺真神奇。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我以前只要花十五分鐘,就可以走到西村(West Village)。現在,在助行器和潔西卡的陪伴下,我可以用極緩慢的速度走到街角那間非常美麗的花店。一直以來,我都很喜歡它的櫥窗──充斥各種繽紛,訴說著四季和節期。我不能買花,因為我仍舊不能靠近花,但它們在我眼前綻放:紫丁香、秋牡丹、貓爪草、鬱金香、水仙花,它們看起來是如此地不可思議,不只是因為它們美麗精緻,同時也因為它們代表春天。它們告訴我們,我們又度過了一個冬天。在歷經邪惡的寒冬後,我活下來了。
多年來,我在第十街上看過許多使用助行器的人。老人,生病的人。過去,我為他們感到遺憾,所以通常我會別過頭去。如今,我為自己之前缺乏欣賞與同理心感到後悔,甚至震驚。此刻我成了虛弱無力的那個人,他們或許看著我,或許避免看著我。我得鼓起勇氣,我必須「承認」,這就是我。我告訴我自己,沒關係,如果你看到我的脆弱,我希望你能對我的勇敢產生敬意。
幾週後,我已經可以一路扶著牆壁、椅子或桌子,走到房間的另一頭了。潔西卡稱之為「家具走路法」。我們的樓中樓公寓裡有一道階梯,它不是螺旋狀的,但它的確有個棘手的轉彎,我不知道我要怎麼靠著它上下樓。幸好,我們家在樓上樓下各有一個出口,所以若要從臥室到廚房,我可以走出公寓,搭電梯到樓下。
有一天,我突然可以自己走路了。
又有一天,我看著樓梯,心想,我可以走下樓。我做到了。更神奇的是,過幾天,我可以爬樓梯上樓了。
──
我的身體越來越有力氣,不過我不寫作了。在我生病這段期間,我手上的兩份劇本計畫也無疾而終。我不覺得自己能夠坐在工作室的電腦前想出任何題材。這對我影響甚鉅,因為我生來就是要寫作的,這關乎我的心理健康,是我的安慰。但寫作已離我遠去了。那一大部分的我,已經在小船中隨著水流越飄越遠了。
彼得是我極大的安慰。我的大腦或許不那麼好使,而且可能再也無法寫作了,但在人生的這個季節,我們竟能找到彼此,每每想到此,我總是讚嘆不已。
彼得很快就甩開了醫院的那些痛苦,不去想它們。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辦到的,但他在情感上一向很堅強。他說,他的韌性來自於走過母親猝死後的傷痛、他所受的醫學訓練,以及多年來承擔病人們的創傷重擔。我需要找人傾訴我的創傷──我仍然會想著威克瘤,我總覺得自己在生活上很笨拙,我害怕獨自出門──而他總會聽我說。不過他也總是注意到我的進步,並不斷在這方面提醒我、鼓勵我。隨著日子過去,我的胃口越來越好,身體也強健了起來。朋友來探望我,我很享受與他們共處的時光。彼得也很高興,他說,我出院後的這幾個星期裡,看著我逐漸痊癒,讓他欣喜若狂。
我是如此幸運,有彼得和摯友陪同我踏上這趟旅程。因為他們知道我歷經了什麼,我也因此沒那麼孤單。在我和每個人之間,有一道鴻溝,我所愛的親朋好友和工作往來對象,都在鴻溝的另一端,因為創傷會孤立一個人。我想到了諾拉。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活著,我的姊姊卻死了,這讓我內心充滿了罪惡感和困惑。我活著,她死了。這看似不可能,但顯然發生了──雖然我也無法完全肯定自己是否能活下去。
我不斷地檢視各種事實。當我姊姊生病時,單倍體臍帶移植法尚未問世。如果當時已經有這種方法,她會選擇移植嗎?她會因此活下來嗎?我永遠都不會知道答案。我希望她能擁有這種機會、這種選擇。由於她決定不要受苦,所以在研究過骨髓移植、尋找配對骨髓後,她最終決定不走這條路。
我不是我姊姊,我的白血病也不是她的白血病。除了我們的疾病在顯微鏡下呈現不同樣貌外,我們選擇度過生病期間的方式也不一樣。我讓自己被朋友環繞,她則傾向不要透露任何消息。身為一個名人,公布這樣的消息要面臨更大的壓力,和一般人的考量是不同的。她研究了所有相關科學知識,也諮詢了許多專家。她曾經是一名記者,那是她事業的起點,而且記者會搜集需要知道的所有資訊並加以分析。我不一樣。我所寫的東西主要來自內心,所以我盡量不去研究這些資訊。姊妹之情有時候是很糾結的──她和我之間的界線不總是一清二楚,諾拉總愛說我們「有一半的腦子長得一樣」──然而當我們生病時,我們顯然相當不同。
我知道,治癒白血病的過程,在心理與生理上都讓我完全耗竭,所以我需要每一份友誼,好支持我繼續走下去。即便諾拉已經不在了,但她仍透過我們的朋友與我一起歷經這趟旅程。
──
麥蓋兒要搬家了,她和瑪蒂要帶著毛奇要搬到奈亞克(Nyack)。怎麼會這樣?誰會想要離開第十街呢?想到此就讓我傷心。在我進行移植莫約一年前,瑪蒂從紐約大學社工系教授和社工師的職位退休了,麥蓋兒最近也開始減少看診人數。麥蓋兒認識我們公寓裡的每個人。我在生病時緊緊地抓著她,但我想我只是仰賴她的智慧與心靈的許多人之一。我還是很難為自己的重獲新生感到喜悅,於是一直向她傾訴我那幽暗的憂慮。
「這一切還是有可能化為泡影,」我說,我無法讓自己更正向,只能絕望地說,「我沒辦法享受當下。」
麥蓋兒告訴我,她不明白我的意思。「對每個活著的人而言,恐懼是生活中的背景雜音。」她說。
換句話說,恐懼會一直在那裡,你是無法逃離的。
我很早就學會這門功課了。在與我母親同住的歲月裡,我學會了這件事,因為她讓我心生畏懼。打從十一歲起,每天晚上我都膽戰心驚,因為我的父母會爭吵、咆哮,我酗酒的母親像被鬼附身似的發瘋狂癲、大吼大叫、摔門而去。我會用手指塞住耳朵,偷偷稀釋她的酒,將枕頭蓋在頭上,躲在毯子或床底下。每一天,我都擔心著當天晚上會不會出事,而結果通常是肯定的。當我們剖析每個人的人生經歷,會發現人人都活在過去經驗的陰影下並受其影響,而我在幼時就已經慣於活在恐懼和擔憂中了。我的大腦很熟悉那種感覺,不論眼前如何光明、不論我擁有多少愛和健康,我總會朝著那個方向去。
我和茱莉亞之間的友誼教會我一件很特別的事:並不是每個人都像我一樣,時時刻刻都在憂慮。她就不是如此。茱莉亞是個陽光女孩,她沒有受過心理創傷。邪惡的帕金森氏症正在使理查緩慢地退化──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跌倒,最近,他甚至接連跌斷了手腳。情況很慘烈,她也跟著受苦,但她從未陷入焦慮。恐懼不是她童年時期的朋友。她會感到恐懼,但她也懂得放手。不過我被制約了,我的大腦為恐懼預備了棲身之所。
(摘自:《老派情書》,〈第七部: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