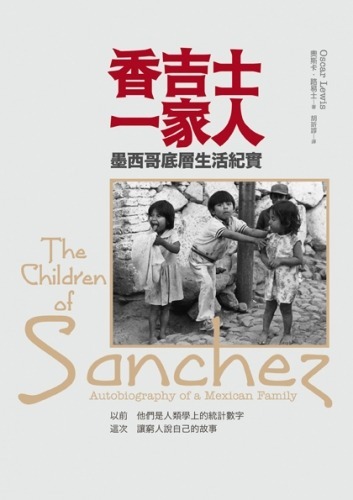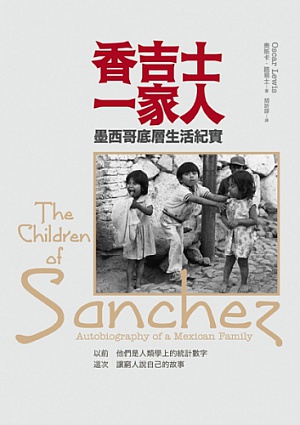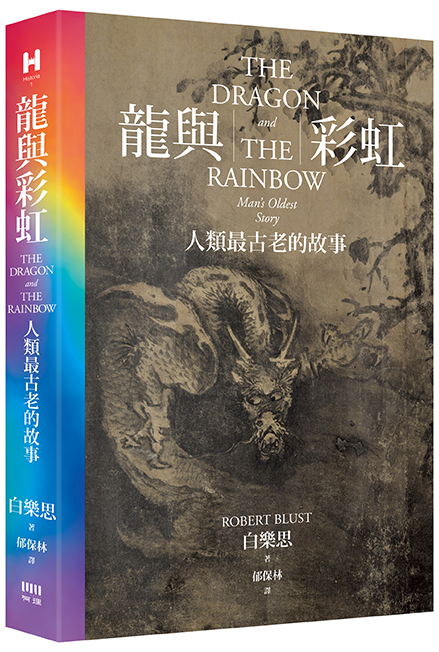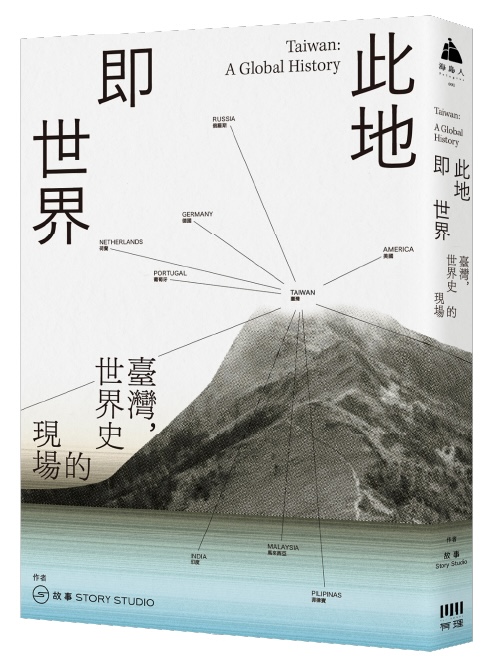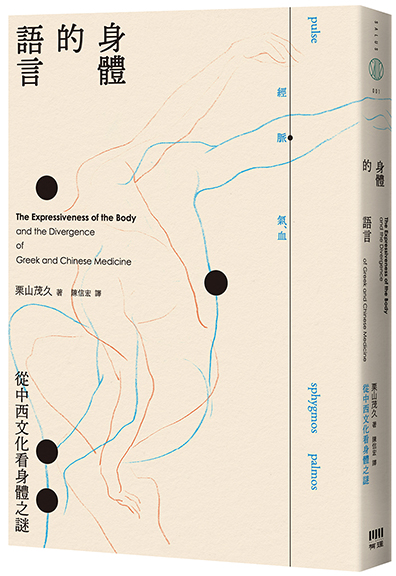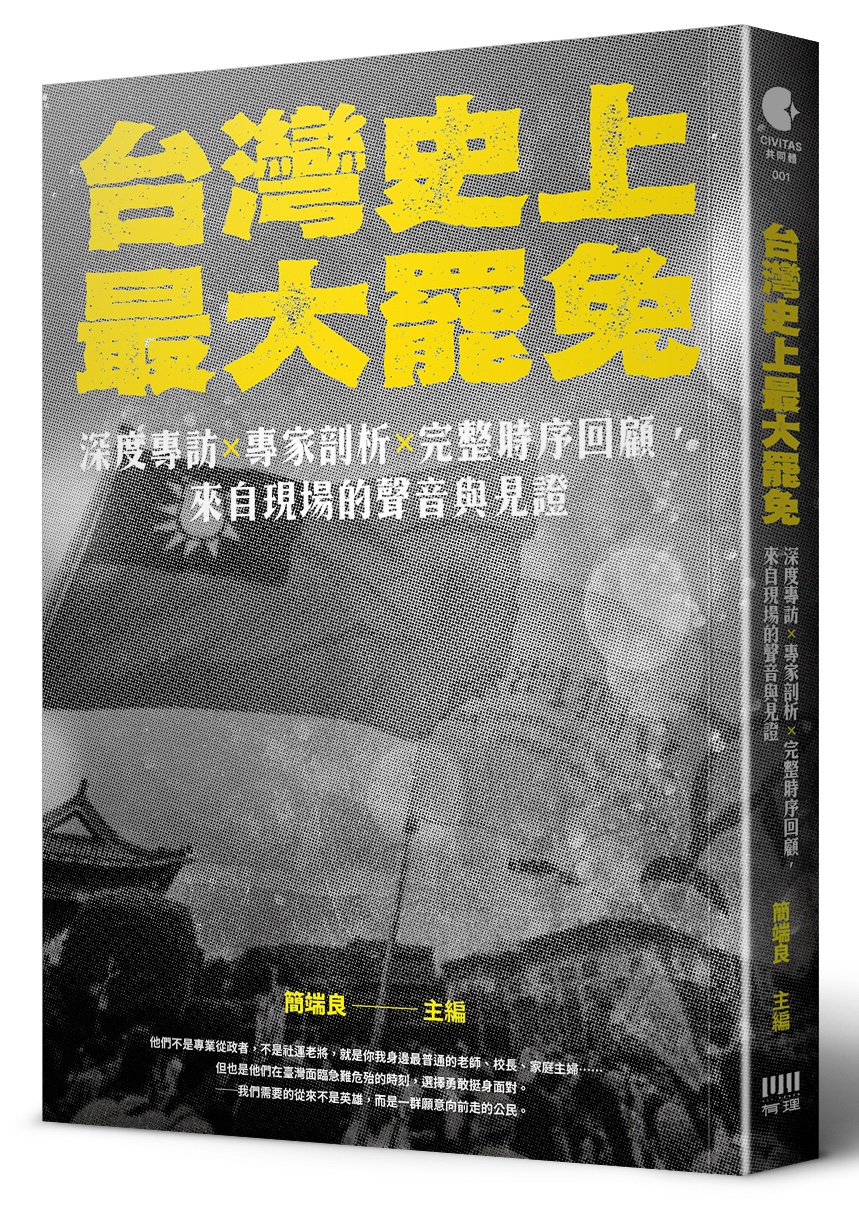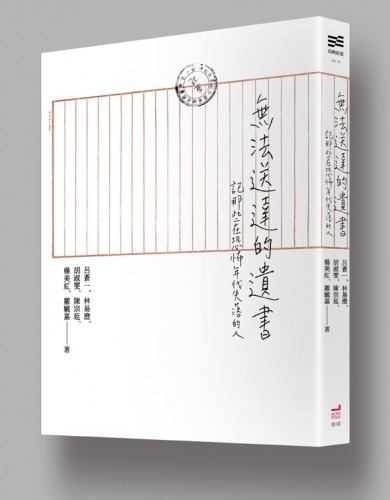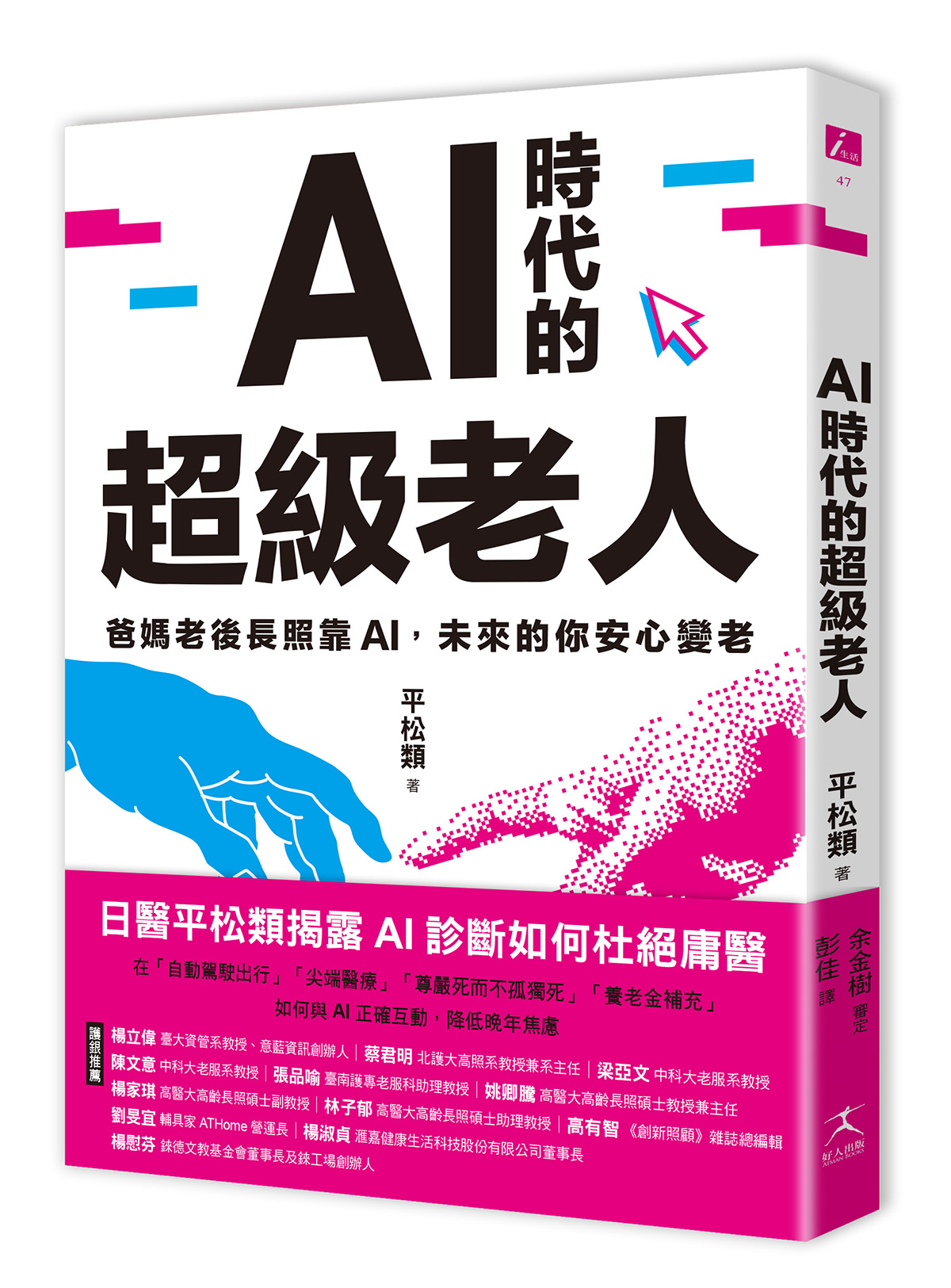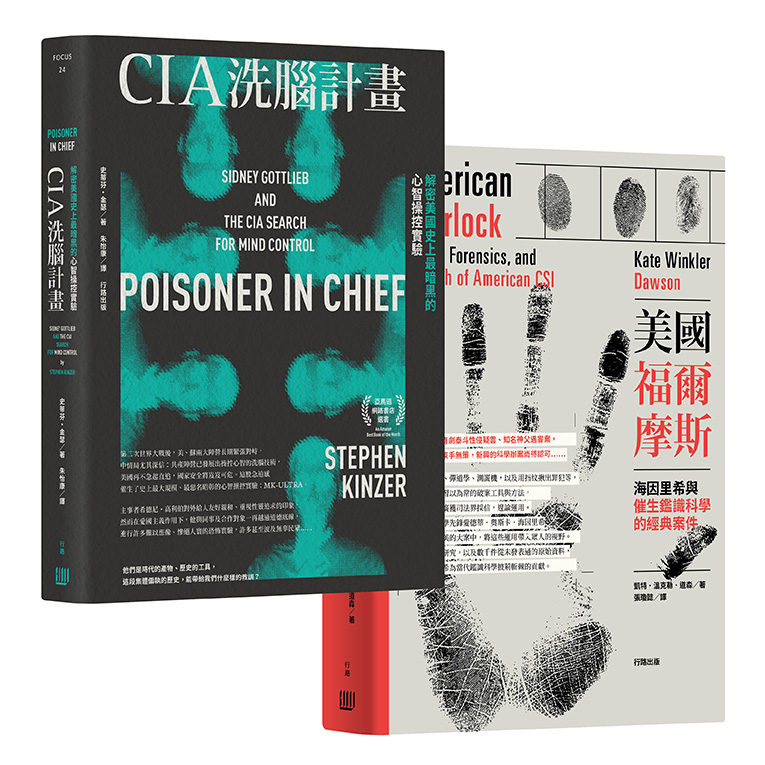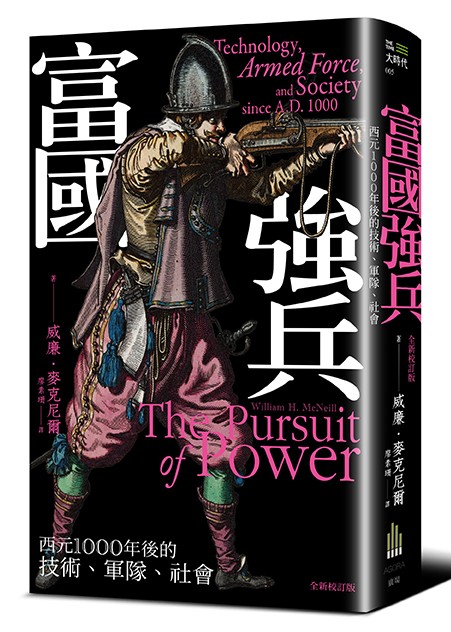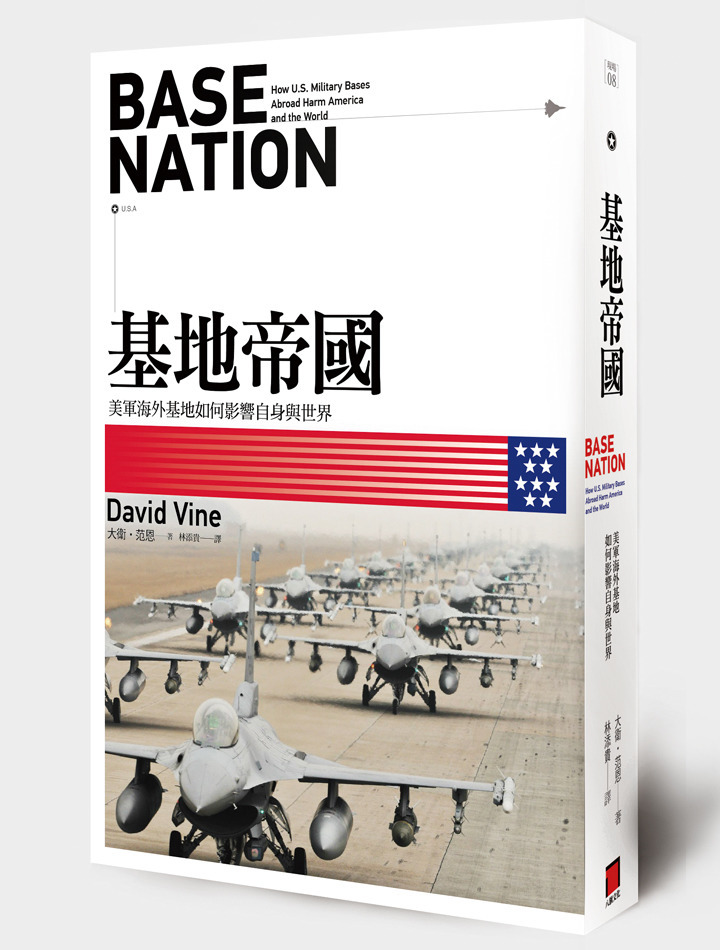以前,他們是人類學上的統計數字。
這次,讓窮人說自己的故事。
有時我對於富裕國家裡的人感到害怕……
他們完全忘記貧窮是什麼感受,而且我們不再有感覺,也
不再與不幸的人談話。――英國文學家斯諾(C. P. Snow)
奧斯卡‧路易士成功了,他選擇了能言善道的受訪者,
在殘酷的世界中喚起人們的惻隱之心。――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
貧窮不只是經濟上的劣勢,它是一種生活方式,穩固且長久地由家庭世代傳遞,有獨特的社會心理,形成一個次文化。
路易士從一九四三年開始在墨西哥做研究,花了數百個鐘頭和這一家人相處,參加他們的舞會與節慶,和他們一起上教堂、看電影,以人類學家的同理心,來認識他們的生活。他用了新的研究技巧,請家庭裡每一位成員用自己的話、說自己的故事,從一個家庭的角度,生動地描繪墨西哥底層生活的各種面貌。
五十歲的一家之主赫蘇斯‧香吉士與他四名成年的子女,親自講述墨西哥貧民窟(他們稱為家的地方)的生活:暴力、死亡、背叛、犯罪、家庭紛爭,一點也不乏味。當然他們也有強烈的情感與人情溫暖,懂得找樂子,對美好人生有所企盼,也渴望去愛與被瞭解;願意分享個人僅有的小事物,即使面對種種難題,仍勇敢地堅持到底。
路易士將香吉士一家人精彩的一生交織成動人的故事,而最終的悲劇,引人同情、憐憫、困惑,令人唏噓不已。
奧斯卡‧路易士(Oscar Lewis, 1941-1970)
出生於紐約市,於紐約州北方一座小農場長大。他於一九四○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先後於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與華盛頓大學任教,之後協助伊利諾大學成立人類學系,並於一九四八年起在該校任教直到過世。
他從一九四三年第一次拜訪墨西哥起,墨西哥鄉下與城市的居民便成為他的研究興趣。除了《香吉士一家人》之外,其他有關墨西哥的著作還包括《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等。另與妻子茹絲.瑪斯洛.路易士(Ruth Maslow Lewis)及蘇珊‧里登(Susan M. Rigdon)合著《活在革命的日子:當代古巴口述歷史》(Living the Revolution: An Or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uba)。
路易士在學術期刊與流行雜誌中廣泛發表文章,並多次獲得知名獎學金與贊助,包括兩次古根海姆獎學金。他也是美國人文與科學院研究員。逝於一九七○年。
序曲:赫蘇斯‧香吉士
我可以說,我沒有童年。我在韋拉克魯斯州一個又窮又小的村子出生,真的很孤單又很可憐。鄉下的孩子不像都市的孩子有那些機會。我父親不准我們跟任何人玩,他從來沒買過玩具給我們,我們一直都很孤單。我只上學一年,大概是八歲或九歲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住在一個房間,就像我現在住的房子一樣,只有一個房間。全家都睡在那裡,每個人有自己的小床,用板子或箱子做的。早上起床後我會先劃十字禱告,接著洗臉漱口,再去提水。吃完早餐後,如果他們沒叫我去樹林裡,我就先坐著等。通常我會帶著彎刀和繩子,去野外找乾的木頭,回來的時候背上帶著一大捆,那就是我還在家時的工作。我很小就開始工作了,我根本不知道怎麼玩耍。
我父親年輕的時候是騎驢的,他會買東西,然後載到遠一點的鎮上賣。他完全不識字。後來他在我們出生的村莊附近擺了個小攤,又在另一個村子開了一家小店,我們就搬過去。他去那裡的時候口袋裡只有二十五披索,不過他用這一點資金創業。他有個朋友賣他一隻大母豬,收他二十披索。那隻大母豬每次都幫他生了十一隻小豬,那時候一隻兩個月大的豬值上十披索。一個人如果有個十披索就可以被稱為「先生」了!披索真的很有價值!這就是我父親如何從無到有,憑著他的毅力和積蓄,他也可以抬頭挺胸。他開始學著思考,幫他的帳戶多加些數字。就靠著自己,他也學會認字。後來他在瓦琴南果(Huachinango)開了一間更大的店,裡面放了更多貨。
我追隨我父親的腳步,把我的開銷都記下來。我把小孩的生日寫下來,彩券的號碼也寫下來,還有買豬花的錢和賣掉賺的錢。
我父親很少跟我說到他自己和他家人的事。關於他的事我只知道他的母親,就是我的祖母,還有一個人是我父親一半血緣的兄弟。我們不知道他父親是誰,我也完全不認識我母親那邊的家人,因為我父親從不和他們來往。
沒有人可以幫助我父親,你知道我的意思,有些家庭,他們處得不好,就像,比方說,我女兒康蘇薇若和她的哥哥們,他們之間有點不合,然後就各走各的了。我父親和他那邊的人就是那樣,他們分開住。
在我自己的家裡,我們比較團結,但我哥哥長大後也都離家了,也是各走各的。因為我年紀最小,所以我留在家裡。我大哥去從軍,在一次意外中死了。他的來福槍走火,自己斃了自己。然後二哥毛利西歐,他在瓦琴南果開了第二家店,第一家店革命的時候關了。他當時在第二家店,有四個男人進來搶劫,他抓住其中一個,而且還抓了那個人的槍。但另一個人從背後襲擊他,他就死了。他很快就死了,肚子還被剖開來,那是二哥。我還有個姐姐尤塔琪亞,她死在瓦琴南果,她那時很年輕,才二十歲。再來是我另一個哥哥李奧普多,他在墨西哥城的醫院裡死掉的。五個兄弟姊妹,其實有六個,第六個很小就死了。我這胎是雙胞胎,我們有五個兄弟姊妹,我是家裡僅存的一個。
我父親不是一個疼小孩的人,自然而然和大部分的一家之主一樣非常節儉。他從來沒有注意到我需要什麼,在鄉下也沒什麼好花錢的,沒戲院、沒電影、沒足球、什麼也沒有。現在生活豐富多了,當時什麼都沒有。所以每個禮拜天,我父親會給我們幾分錢花用。世界上有各種人,不是每個父親都會寵小孩。我父親相信太關心小孩會毀了他們,我也相信。如果一個人太寵小孩,小孩不會長大,不會獨立,他會很膽小。
我母親在一個小鎮出生,我記不得那個鎮的名字。她不多話,我是最小的,她從不跟我說什麼。我母親很安靜,心腸很好,給我很多愛。我父親固執、嚴厲,比較衝。我母親是一個正直善良的人,對任何事都很認真,包括她的婚姻生活。但我父母會吵架,因為我父親有另一個女人,我母親很嫉妒。
我父母分居的時候我大約七歲。革命把店給毀了,生意結束了,房子沒了,我們的家破碎了。我自然跟著母親,還有一個在糖廠做工的哥哥,我也在田裡工作。兩年後母親病了,我父親騎著驢子來看我們。我們住在一個很小的破屋子,只有一邊有屋頂,另一邊暴露在外。我們跟人借了一些玉米,因為真的沒東西吃,我們非常非常窮!也沒有藥或什麼的給我母親,沒有醫生,什麼都沒有。她回去我父親的屋子,然後死了。他們兩人在最後和解了。
唉,我母親死了,我的厄運就開始了。我大概十歲的時候搬去和我父親住,我在那裡住了兩年就離家去工作了。我們很久以後才有繼母,那時我早就離家了。我父親在那裡娶了一個女人,那個女人簡直是搶劫,她和她的兄弟把所有的東西都拿走,還把父親丟到街上。有一天晚上,他們為了錢差一點要殺了他,鄰居擋下來,那個女人才離開。那段婚姻是有法律效力的,那個女人聯合那裡的人把他的房子和財產都拿走了。
後來他又在同一個鎮的另一邊買了一個小房子,又開始做生意,但那時他病得很重。的確,有時候我們男人想要很強壯、很威猛,但說到底,我們不是。談到生死或家人的事,就像在心頭上扎針一樣,想到一個男人孤單的哭就令人心痛。你一定發現很多人整天喝酒,有些人抓了把槍就自我了斷,因為他們不能承受內心的感受。他們找不到管道表達,也沒有人可以訴苦啊!所以他們抓把槍,就這樣,結束了!有時候那些相信自己很勇猛的男人,當他們單獨面對良心的時候,真的不是那樣,勇猛都是吹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