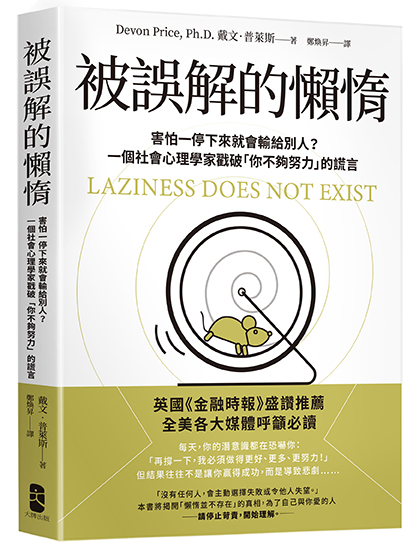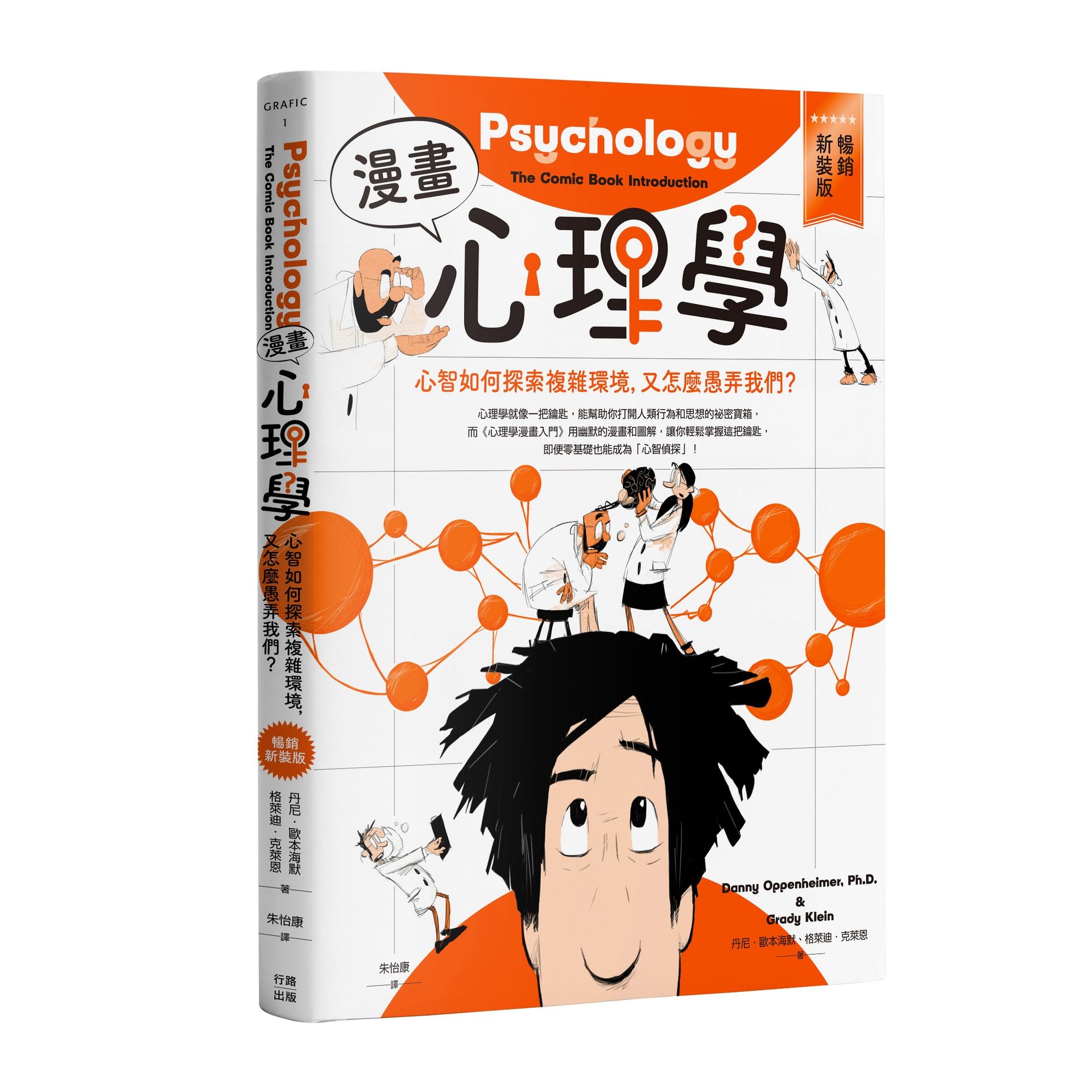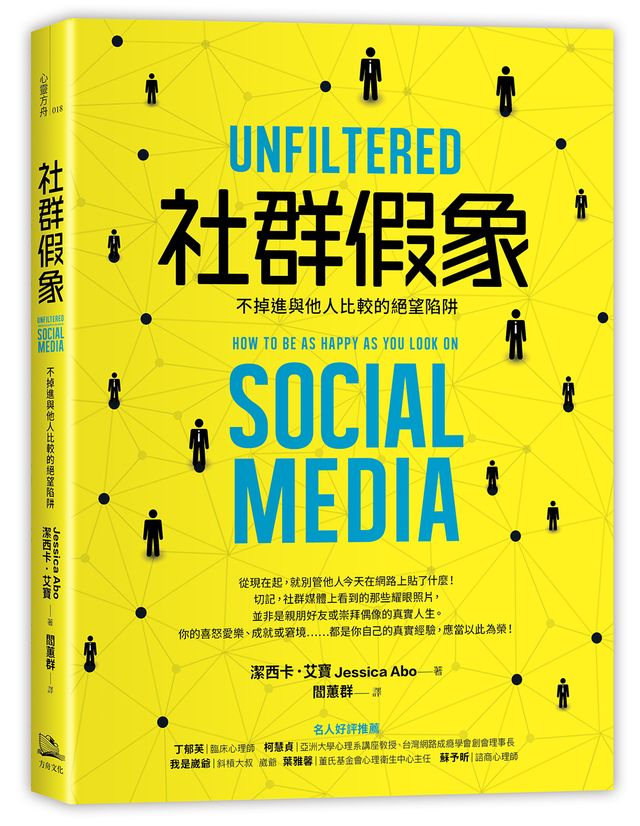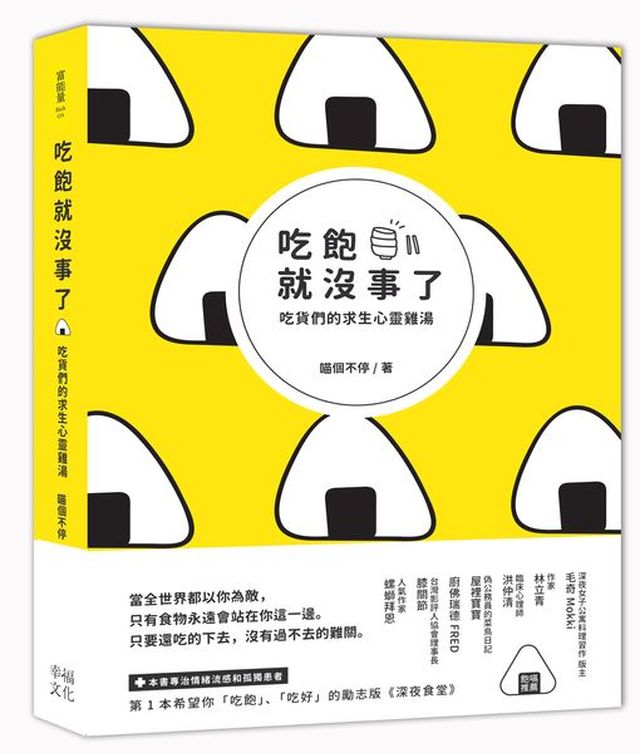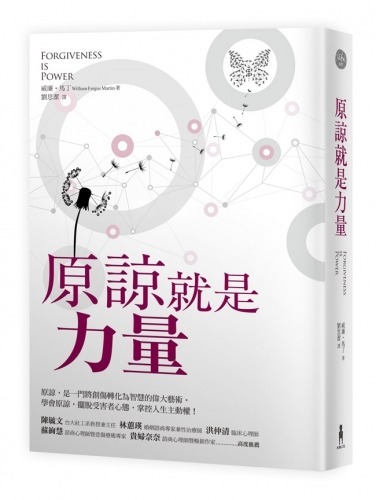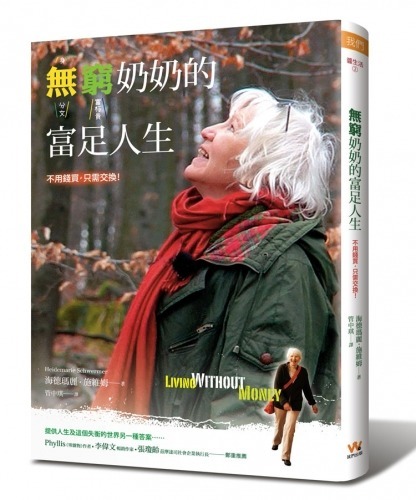「但凡有生命的存在,必然也會面臨死亡,誰都無法自外。
然而每當有人死去,那麼我的工作便開始了……」
黴菌叢生的牆面、充滿穢物與動物屍體的地板、
散落的藥袋或雜物、被血水浸濕的棉被……
你曾經想像過那樣孤單寂寞的風景嗎?
穿梭在各種死亡現場的「遺物整理師」,
一邊清理死亡現場的血跡與遺物,一邊思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這些曾在懸崖邊掙扎的生活痕跡、不分年齡與性別的孤獨死亡,
既沉重、哀傷,又充滿了對社會的無限諷刺。
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更有價值。
◆清理往生者留下的血痕及生活用品,在死生交替之地工作的「遺物整理師」
在遺物整理師的工作場域,充滿了各種「死亡故事」:自殺臨死前做好資源回收分類的女子、自殺前先諮詢了整理費用的中年男子、詢問如何無痛自殺的女子、一同躺著迎接生命終點的夫婦……
隨著遺物整理師金完的視線,我們目睹了每一條生命在踏上死亡之路前的孤獨與絕望。
「我經常出入自殺現場,目睹奪命的手段仍然留在現場的情景。解開掛在陽臺、天花板或天然氣管上的晒衣繩,將野營用簡易火爐上堆積如山的木炭灰燼抖落,那都是我必須做的工作。」
◆以某人的死亡維持生計是種諷刺,懷著罪惡感,也肩負著社會責任
「清掃亡者的家時,曾見過鬼嗎?」
「工作時不覺得痛苦嗎?」
「完成工作後有什麼意義?」
從事特殊清潔的作者金完,不時會收到類似的提問與媒體關注。然而,生與死就像硬幣的兩面,只有單面是不成立的,在死者離開人世的地方,其實會更鮮明地展現他的生活與存在:尚未寄出的履歷表、使用多次的搬家箱子、信箱裡的催繳帳單、一落一落的心理勵志書……
隨著「孤獨死」時代的來臨,遺物整理師在死亡現場見到的,是不分年齡與性別,隱藏在陰暗角落裡的掙扎,以及不得不屈服於社會框架的悲鳴。
「靠死亡維持生計是這個職業的諷刺,但我相信這些紀實內容會產生作用,這是一種社會責任的自覺,激勵我繼續寫作。」金完深信,這些針對死亡的細緻陳述,終將成為病毒抗體般的存在,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更有價值。
「在決定自殺後,還擔心善後工作的男人;自己打電話打聽死後清理價格的男人。這世界到底有什麼無血無淚的殘酷事由,將一個人推向窮途末路還不夠,還逼著他要預先擔負活著的人為死者留下的東西清理的代價?」
【熱淚推薦】
如果人的一生像部電影,那麼作者金完的工作,就是在電影片尾名單中的最後一行,如果不定睛看很容易就會忽略。透過這本書,作者將在我們周遭默默離去的人們最後疲憊的身影照亮,反過來傳達人生的強烈意志與珍貴。
──柳成昊(首爾大學醫學院法醫系教授、《每週都去看屍體》作者)
金完(김완)
出生於首爾,在釜山長大,大學時主修詩文創作。
曾在出版業與趨勢產業領域工作,為了成為專職作家,在三十多歲時突然展開了山居生活。
之後的幾年裡,曾滯留日本進行採訪及寫作,開始對逝者留下的物品、打理其身後事方面產生關心。在經歷311大地震後回到韓國,成立了特殊清潔公司「Hard Works」,一邊工作一邊記錄自己平時在死亡現場面對的「人的生命與存在」。
序|打開門的第一步
第一章|清掃某人獨自離開的地方
野營生活
資源回收
去開滿漂亮花朵的地方吧!姊姊
窮人之死
黃金,總有一天也會像石頭
尿液嘉年華
抱起貓咪
地獄與天堂之門
書架
棉被裡的世界
隱藏的東西
雙雙棒
致親愛的英珉
第二章|做有一點「特別」的工作
特別的職業
將房子清空的樂趣
野芝麻
凶宅的誕生
救你?還是救我?
價格
望著鍋蓋的心
打掃洗手間
如紙鈔般鐵青的臉龐
Homo faber
渺小夜晚的鋼琴演奏
後記
作者序
打開門的第一步
手拿著兩個扁平粗糙的黑箱子,按下按鈕,靜靜等待停在高處的電梯下降到我所站立的一樓。每回初次來到現場,電梯總讓我感覺像寄居在遠處的陌生存在之物。幾次習慣性地抬起頭來,看著原是兩位數的紅色數字漸漸變得越來越謙虛、越來越小。雖然視線落在電梯門上顯示的數字,但那一個個數字的意義並未深印入心裡。或許,在電梯前的時間,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以同樣方式公平地流逝的吧!上個月離世的您,生前也曾立在這道門前,或許每一次的等待都很短暫,但是累積下來應該也算度過了很長的時間了。彼此互不相識的我們,從這一刻開始共享這個時間。
以厚度四釐米、強韌的聚丙烯製成的箱子裡,裝有各種防護工具。藍色手術手套、同樣也是藍色的鞋套,另外,還有以透明藍色塑料製成的另一組鞋套。白色的防塵口罩、淺灰色防毒面罩,以及開門的必備工具等,全都分裝在兩個有把手的箱子中。這些防護工具對於我這種職業的人來說,等於是另一層皮膚。就像保險套可以防止生命孕育一樣,我相信這些防護裝備的薄膜可以防止我受到感染、污染、死亡的威脅。
曾經是遠處陌生存在的電梯,現在爽快地向左右敞開胸懷,帶著我一起上升到指定樓層。此刻,鼻子變得比任何時候都要敏感,我下意識地在電梯裡搜尋。上了年紀的男人慣用的古龍水香氣、剛送來的披薩,還有廚餘也好像曾停留過,落下若有似無的難聞氣味……在密閉的空間裡,嗅覺的追蹤能力提升到極大值。電梯門打開,把我趕了出去,這個追蹤變得無比執著。其實我的工作,是由往生者製造、折磨活著的人的味道所帶來的。在積極去除那些氣味之後,我的工作就完成了,而活著的人會支付給我代價。
請原諒我。即使到了門口,我也不會按門鈴,因為在裡面等著我的並不是您,而是您留下的東西。小心翼翼地打開黑色箱子,套上鞋套,戴上手術用的手套,仔細檢查確認沒有任何鬆脫或可能遺漏之處;先暫時不使用任何可以遮掩口鼻的防護口罩,因為未經任何過濾地嗅聞氣味,這項事實性的測定,是我規劃工作流程與成功交差的基準。現在我就像策劃完美犯罪的人一樣,不留下指紋、腳印與任何痕跡,一如往常自然地抓住大門把手,毫不猶豫地進入屋內。
打開門,邁出第一步,習慣性覆誦「超脫吧」的決心黯然失色,我的鼻子已被亡者留下的氣味淹沒,心臟邊緣籠罩著昏暗潮濕的陰影。雖然找到開關打開了電燈,但這一瞬間的光並未進入我的心裡。像深夜裡行進在沒有路燈的鄉間道路上,車燈所照明的世界,視野變得狹窄。喉嚨裡像風掠過鹽漠一樣沙沙作響,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在海底緩緩游動的深海魚。氣味的發源處是有著一線光明的地方,魚在黑暗中慢慢地游向那微弱的光芒。為了避免被隱藏在沙子裡的珊瑚和擱淺在深海各處的遇難船隻殘骸刺傷,必須盡可能緩慢地前進。
眼黑心弱的魚兒啊!
必須克服恐懼游去那裡,
只有這樣才能從嚴酷的深海壓力中釋放出來。
長期放置屍體的地板必然有一層油膜,為了避免滑倒,必須繃緊神經往前走。那個房間就是您嚥氣的地方。
雖然您不在了,但肉體留下的碎屑仍若無其事地待在那兒,床上乾涸的黑紅斑點誇張地顯示軀體大小。枕頭上,生前在您後腦勺的皮膚與斑白的頭髮也一起乾涸。附著在天花板和牆壁上的肥大蒼蠅,應該正默默地搓著手掌吧!翻開被子,終於找到在奶蜜之鄉擠在一起溫存的蛆蟲們,彼此蠕動摩擦著身軀。看到蛆蟲蠕動全身跳舞的畫面,我那彷彿被剝製成標本、裝在有酒精的玻璃罐裡的大腦,重新找回了溫度,開始活動。原本變窄的視野這才像是離開隧道一樣逐漸明亮,我來此的目的也清晰地浮現出來。在這裡新誕生的小生命告訴我,是該將步伐朝往另一個方向移動了。
從房間出來,為了掌握這屋子裡各種物品的規模,我開始探索。經過客廳到陽臺,浴室到另一個房間,再經過廚房到玄關鞋櫃。步伐快速移動,原本投射在心上的陰影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曾勒緊心臟的黑暗,若遇見「具體直視真相」的強烈太陽,通常就會消聲匿跡,像是從未出現過一樣。恐懼總是從心裡開始,又消失在心裡,從來就沒有露出過。
您在這裡獨自結束生命,並停留了很久。今天,我會將您留下的痕跡,以專業技術清除掉。不過現在,我要先打開門走到外面,再搭電梯到一樓。那裡,剛辦完葬禮的您的女兒正在等著我。在等待電梯的期間,我得先想想待會該怎麼跟她說。
好,現在我要把電燈關了。
書摘
資源回收
真的曾有人死在這屋內三個月嗎?
抵達三樓玄關門前,等待我的只有像是走廊一樣漫長的黑暗與寂靜。若不是事先已經聽過了說明,根本就不會料想到裡頭發生過什麼事。站在門前也沒有聞到象徵亡者自我介紹一般的特有味道,只是隱約感覺到走廊盡頭的牆壁上,似乎已噴灑了一段時間的檸檬芳香劑。
建築物的一樓,是被稱為「架空層」(piloti)、將房屋底層架高挖空建造的停車場,是現代典型的都市生活住宅。二樓以上每個樓層隔著走廊,左右兩邊都各有六間獨立套房相對。令人驚訝的是,在這棟狹小的建築中,竟然有二十多戶獨立家庭。而這棟建築周邊的建物,結構也都相差無幾,就位於將偌大的工廠園區團團圍住的所謂one-room村的南側邊緣。
按下六個數字,信號音響起,同時玄關門也解鎖了。一開門就聞到與走廊空氣相異的難聞氣味,像是吞下沾了過多芥末的壽司一樣,氣味瞬間直衝鼻腔。進門後我立刻把門關上,同時想起在與委託工作的屋主通話時,他再三叮囑的話語。
「那件事目前還沒有人知道,要是被知道了,房客一定全都會搬走的,所以千萬不能被住在那棟樓裡的任何住戶發現。」
我本能地走向窗邊。先透透氣吧!接下來再進一步掌握狀況。窗戶一如預期地不容易打開,因為窗框四周牢牢貼著青綠色的膠布,那是為了防堵室內空氣流通才故意貼上的。我拿出小刀,把膠帶的一角挑起來,再用拇指和食指抓住,慢慢地用力撕起。伴隨著撕裂的聲音,膠帶好不容易撕開了。膠帶上橫的豎的密密麻麻的網紗附著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的痕跡。打開窗戶,這才終於能夠正常呼吸。如果將埋怨這個世界毫無慈悲的往生者棄置在這裡任其長久腐爛,那這氣味也同樣毫無慈悲可言。
亡者所準備好的完美密室。為了確保使用炭火可以毫不失手地殺死自己,她進行了澈底的準備:玄關門上下左右的縫隙用青綠色膠布仔細封住、門下方有個可以投遞牛奶或報紙的圓形投放口,也用膠帶橫著貼了好幾層,密密實實地封死了。浴室的排水口和抽風機,還有瓦斯爐上的瓦斯氣孔及水槽的排水口,屋內所有的孔洞都完美澈底被堵死了,就像慎重地把每一顆釦子牢牢扣上。經過一連串密封的過程,然後在浴室地板放了露營用的簡易火爐,再放上幾塊炭,將火點燃。
床墊上有兩個乾涸的圓形血跡,相連在一起像是黑色雪人般十分鮮明。長長的皮膚組織就像脫下的褐色長筒絲襪一樣,蜷縮在一起。鏡子前的各種化妝品容器之間,立著兩個沒有照片的空相框。
我把散落在浴室地上的煤灰掃乾淨,突然想到:
「火爐周圍並沒有像打火機之類的點火裝置啊!」
沒有噴槍,甚至連生日蠟燭會附的火柴都沒有,那是用什麼方法點火的呢?與其他燒炭自殺的現場相比,這火爐的周圍算是很乾淨的。屍體被發現時,救護隊員和警方的鑑識人員一定都先處理過了,但我從未遇過還會幫忙清理現場的,反而多半都是留下收拾屍體時使用的手套、鞋套、紗布等消耗品在現場。向來只有製造垃圾,從未有減少垃圾之事。委託人說,這個地方連亡者遺屬都沒有來過。
我的疑惑在清理大門左側的家用型垃圾分類回收箱時解開了。為了區分資源回收物及一般垃圾而分成四格的回收箱中,藏了所有消失的物品。生火用的噴槍及瓦斯罐都在金屬類的箱子裡、火爐的包裝紙與快遞紙箱都摺成扁平狀放在紙類回收箱內,瓦斯罐的紅色噴嘴則塞在塑膠類回收箱裡。
在自殺之前做好資源回收分類?這可能嗎?雖然以前曾在其他自殺的亡者家中,發現已經清理好的速燃煤外包裝,但這也太不合常理了。為了結束自己的生命而點燃炭火,在煙霧繚繞中,趁著還未失去意識之前把這些東西一一整理好?在那過程中她到底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在自己瀕死之際還能如此超然的公共道德家真的存在嗎?或者,到底是多麼強大的道德束縛和法律規範,如此冷酷無情地逼迫面臨死亡的人服從?
當我把裝有遺物的袋子拿到停車場,一個看起來五十多歲、個子不高的男子遠遠地走了過來。他問我是不是清理遺物的業者,然後自我介紹說是這棟大樓清掃公用樓梯的人。
「大概三十歲吧?是位很善良的人,很有禮貌,每次看到我都不停地說謝謝,真的就像是把謝謝掛在嘴邊的人……」
他突然開口,我趕緊拉著他到停車場外。
「每年的春節和中秋,她都會準備襪子或是食用油禮盒。」
「原來是您認識的人啊!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您,不過我們現在說的話要是被別人聽到不太好,還是請您小聲一點。」
「是,這我也知道。房東也受到很大的衝擊吧?因為是他自己用鑰匙打開門才發現屋裡的狀況。我有好幾個月沒看到那位小姐,還以為她搬走了,想說她應該不是那種搬走也不說一聲的人,心裡還有點遺憾吶……上個禮拜我來打掃時,看到救護人員抬著擔架從那裡走下來,因為蓋住了,所以我壓根沒想到是人,還想說是狗或貓呢!因為看起來很小啊……等到救護人員離開,房東下樓來才跟我說是住在三○一號的那位小姐。」
男子連手上點燃的菸都忘了,繼續說道。
「總之,請您務必用心整理,總覺得她不是和我完全不相干的人……像她那種人應該過上好日子才對啊……真的不像是陌生人的事……」
在負責清掃大樓的他口中,那位女子非常善良,但那樣善良的人也許對自己並不慈悲,最後成為結束自己生命的人。即使委屈和悲痛堆積如山,也無法對別人惡言相向;也許正是她無法將箭射向他人,才讓自己成為了箭反射後的靶心吧!連殺死自己的工具也要先分類好再丟棄的善良、正直心性,為何不能留給自己呢?為什麼不能成為只對自己善良的人呢?或許正是那顆正直的心,反而成為鋒利的針,不斷強迫地刺向她自己吧?
垃圾袋裡裝滿了木炭的包裝紙,以及從醫院拿的數十個藥袋。她從相簿和相框中取出了許多照片,相片的邊角成了尖尖的鋸齒,銳利地刺破袋子。這一切都是她在臨死前親自整理的,她未完的故事,充滿嘆息與絕望的故事,似乎都原封不動地裝在了這些袋子裡。
有時,這世上各種不知緣由的故事就像被冷風颳過、葉片全都掉落的枯枝,卻能強烈動搖我的心。那種時候,就連丟棄一個小紙袋都覺得格外沉重。